為什麼人們正在辭職並抗議工作生活,從美國到中國 - 彭博社
bloom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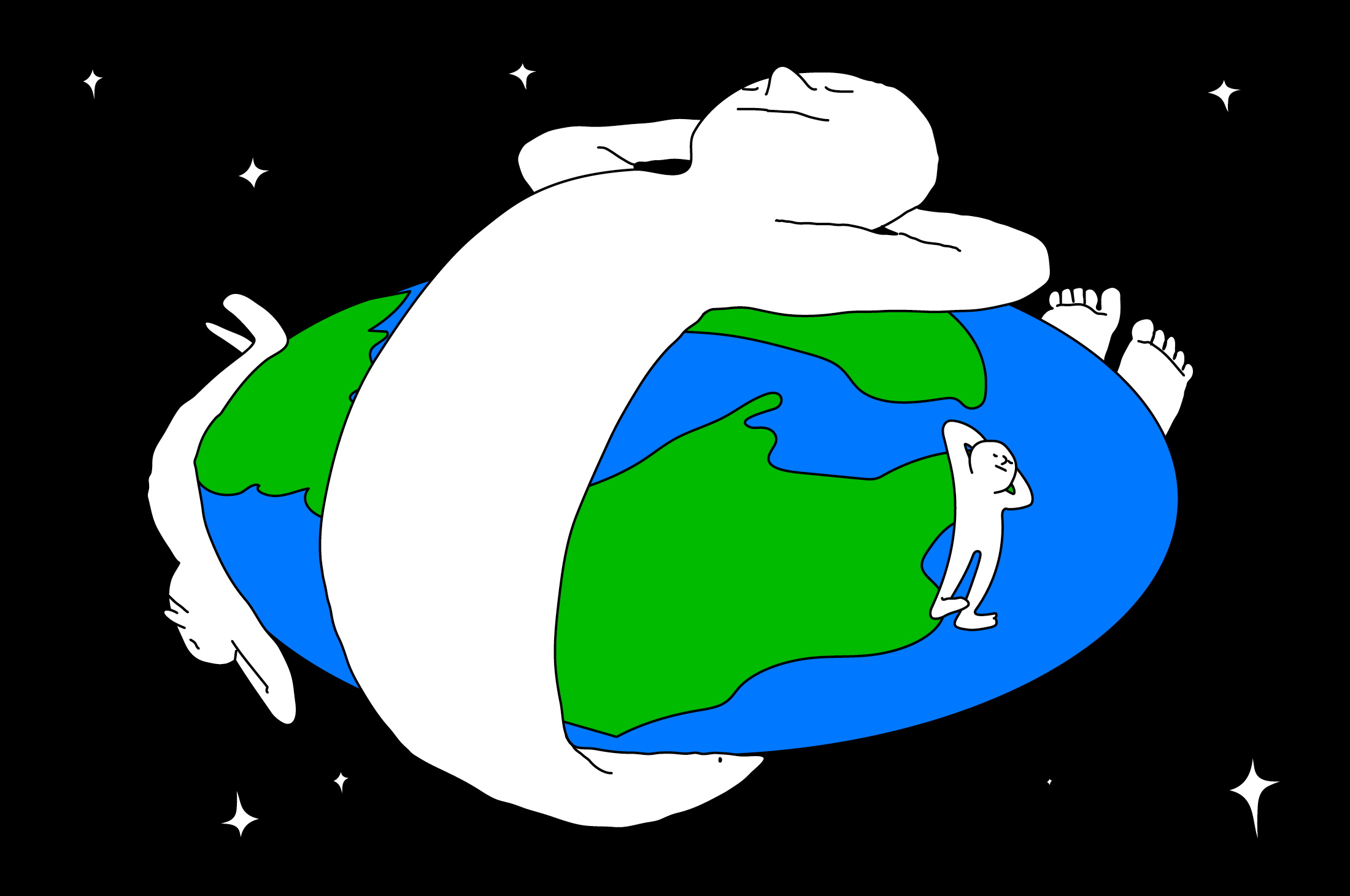 插圖:Chris Nosenzo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
插圖:Chris Nosenzo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
全球範圍內,數百萬人正在重新思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平衡兩者。
美國的“大辭職”現象導致員工大規模辭職——今年4月至9月間有超過2400萬人這樣做——許多人選擇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德國、日本和其他富裕國家也出現了類似趨勢。
大流行病造成了嚴重影響,調查顯示許多國家的人們感到更加疲憊不堪,心理健康狀況惡化。
但發達國家的壓力已經積聚了幾十年。收入停滯不前,就業安全變得不穩定,住房和教育成本飆升,導致越來越少的年輕人能夠建立經濟穩定的生活。
儘管“大辭職”現象主要發生在40歲以下的人羣中,但它也在整個經濟中產生了影響,並促使人們就工作展開更廣泛的討論。千禧一代(出生於1980年至1990年代末)和Z世代(在他們之後的人口羣體)傾向於比他們的前輩晚結婚、購房和生育子女,甚至可能根本不這樣做。
中國的“躺平”運動,由一篇社交媒體帖子引發並得名,也是一種選擇退出的行為。這是對一種殘酷的“996”工作制度的反應——在技術等行業,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是很常見的。家庭、社會甚至政府都施加着持續不斷的壓力,要求人們不斷攀登職業階梯。
這個國家的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翻了一番,但並非所有人都在分享這些好處:在許多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漲超過了工資增長。
因此,一些人將“躺平”現象視為即將到來的日本式停滯的警告——這種停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出現得出乎意料。其他人認為這更像是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和西歐部分地區出現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普通人尋求一個更注重個人發展、壓力較小的社會。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向飈表示:“這兩種論述同時出現基本上是巧合。但我們可以建立聯繫。這涉及到經濟如何變得過熱和不可持續,無論是在環境上還是在心理上。”
根據微軟公司的一項調查,全球近一半的工作者正在考慮辭職。約有四成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受訪者表示,如果要求全職回到辦公室,他們會辭職,這是由諮詢公司Qualtrics International Inc.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發現的——比其他任何一代都要多。
一些年長一代批評這些態度是特權和懶惰。但事實是,幾十年來,富裕國家各個年齡段的工作時間一直在下降。
每名工人的平均工作小時數
在整整一年中
數據來源:Huberman & Minns(2007)和Penn World Table,由Our World in Data編制
面對像疫情和氣候變化這樣的存在威脅,大規模辭職和躺平有潛力引發關於個人和整個國家對財富不懈追求的更深入討論。
“當面對死亡的前景時,人們的行為肯定會有所不同,”Qualtrics員工體驗諮詢服務主管本傑明·格蘭傑説。“人們用非常不同的視角看待工作。這個視角是,‘我不是為了薪水而工作。這不是問題所在。我需要得到滿足。’”
中國的躺平現象
起初是中國年輕人反叛的機智表達,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連習近平都承認的運動。在八月的一次講話中,總統敦促國家“避免內卷和躺平”,而是“為上升通道開闢渠道”。
“我已經兩年沒工作了,我覺得這沒什麼錯,”四月在百度貼吧平台上引發躺平熱潮的帖子寫道。“壓力主要來自與同齡人的比較和老一輩的價值觀。但我們不必追隨他們。”
這位署名為“善良旅行者”的帖主將自己與古希臘哲學家戴奧根尼斯進行了比較,後者是一個生活在木桶裏的苦行者。“躺平是我的哲學運動。”
這場運動的精神家園可能是中國東南部的深圳。這個蓬勃發展的科技中心擁有巨大的電子工廠和華為科技有限公司、騰訊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以及1800萬人口,其中許多人從中國其他地區搬到那裏追求財富夢想。現在,隨着經濟放緩,一些人開始懷疑這些夢想是否值得努力。
傑克,一名32歲的科技工作者,五年前被一家電信公司聘用時充滿雄心壯志。但繁重的工作量並沒有帶來他期望的成功,隨着時間流逝,他的熱情消失了。他仍在工作,但不再那麼努力。
大流行病之後重新思考工作(視頻)
“許多互聯網行業已經達到了沒有爆炸性增長的階段,”傑克説。“但所有的繁重工作仍在這裏。所有的壓力仍在這裏。你會失去希望。”
深圳是世界上最不可負擔的城市之一,這加劇了他的困境。“即使對於像我和我的女朋友這樣薪水豐厚的專業人士來説,情況仍然瘋狂,”他説。“在深圳購房的首付是200萬至300萬人民幣[約31.4萬至47.1萬美元]。那就像我們倆的全部儲蓄,再加上父母的巨大幫助。”
10月份,包括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和抖音的所有者字節跳動有限公司在內的數千名員工參加了一個在線活動,通過在公開的電子表格上發佈他們的工作開始和結束時間,這個活動被命名為“工人的生活至關重要”。字節跳動隨後實施了較短的工作周。
在表情包和網絡帖子中,年輕的中國人將他們的一代稱為“鼠人”和“鹹魚”(在粵語中,鹹魚是屍體的隱喻,但也可以指缺乏抱負或動力的人)。如果這種態度變得普遍,可能會加速人口下降:2020年中國的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這是一個主要關注點,因為勞動力已經在減少。
生育率
每位女性的出生人數
數據:世界銀行
在深圳北部的三和就業交流中心,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十名新移民聚集在一起瀏覽工作崗位。雖然中國的農民工曾經因其勤勞而受到讚揚,但這些男性和女性卻因花時間玩網絡遊戲或觀看電視節目而聲名狼藉,只有在需要支付電話費或房租時才會接一些臨時工作。他們放棄了長期工作和工廠工作,轉而選擇較不苛刻的服務性角色,用一個簡單的口號概括他們的生活方式:“工作一天,玩三天。”
 2018年,深圳三和勞務派遣市場外的求職者。圖片:ImagineChina最近的一個早晨,來自陝西省的32歲的李先生(不願透露全名)毫無熱情地審視着市場的公告牌。當一名招聘人員拿着一段工廠招工的智能手機視頻走過來時,李先生一看到涉及操作重型機械的工作就拒絕了。
2018年,深圳三和勞務派遣市場外的求職者。圖片:ImagineChina最近的一個早晨,來自陝西省的32歲的李先生(不願透露全名)毫無熱情地審視着市場的公告牌。當一名招聘人員拿着一段工廠招工的智能手機視頻走過來時,李先生一看到涉及操作重型機械的工作就拒絕了。
李的態度表明躺平運動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症狀:隨着一個國家變得更富裕,它的工人可以更加挑剔。在美國和歐洲,大規模中產階級的形成是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以及後來90年代所謂的懶漢一代崛起的關鍵。
在對西方運動的迴響中,有着比父母更有希望的前景的中產階級年輕中國人表示,他們的社會過於墨守成規和物質主義。“成功有一個相當狹窄的定義,”正在深圳學習芝加哥大學在線碩士學位的25歲的陳子洋説。
“我們都知道馬雲和那些CEO。但如果每個人都追求那種職業,當然會有更多的競爭和抑鬱,”她在一家高檔茶館喝酒時説。“有些人選擇放棄,躺平。”
美國的辭職
美國千禧一代的財務焦慮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存在。由於學生債務激增和大蕭條後的緩慢復甦,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代比父母更貧窮的一代。
疫情似乎使這些擔憂達到了頂峯。根據Mind Share Partners的一項調查,2021年離職的千禧一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提到了心理健康原因,而Z世代的比例甚至更高,達到了81%。
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也讓許多年輕人開始質疑他們的優先事項。
2020年7月,本·安德森工作的華盛頓特區聯邦機構召集其員工回到辦公室,但沒有提供安全設備,也沒有為保持社交距離做出安排。在一位同事成為新冠長期患者後,安德森開始懷疑是否穩定的工作才是安全和美好生活的關鍵。這位29歲的年輕人説:“當世界崩潰時,我覺得他們根本不在乎我。”
辭職在他腦海中已經有幾年了。他在大學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為了工作搬到了一個大城市,並在一份全職的白領工作中工作了七年。然而,他仍然沒有存足夠的錢買房。“工作壓力巨大,而且我離家很遠,”他説。“在某個時候,我開始想,‘為了什麼?’我在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工作,你無法改變什麼。它不是為此而建立的。我只是變得麻木了。”
他現在住在洛杉磯,在電視節目和廣告中演出。“在像瘋狂的好萊塢這樣的地方,我和在政府工作中冒險的機會一樣多,”他説。
儘管“大規模辭職”通常被認為是青年運動,但至少一項研究顯示,30至45歲的員工也以較高的速度辭職。
 內特·曼(Nate Mann)坐在他在華盛頓特區家中的藝術工作室裏。攝影師:迪·德懷爾/彭博社內特·曼,現年40歲,是最年長的千禧一代之一,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酒吧當了將近一半的人生。他忍受着深夜和高壓力,換取大約每年8萬美元的收入。但是,當新冠疫情於2020年3月關閉了他工作的酒吧時,他決定專注於一直在兼職做的事情:繪畫。
內特·曼(Nate Mann)坐在他在華盛頓特區家中的藝術工作室裏。攝影師:迪·德懷爾/彭博社內特·曼,現年40歲,是最年長的千禧一代之一,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酒吧當了將近一半的人生。他忍受着深夜和高壓力,換取大約每年8萬美元的收入。但是,當新冠疫情於2020年3月關閉了他工作的酒吧時,他決定專注於一直在兼職做的事情:繪畫。
“突然間我有了這麼多時間,所以我就埋頭專注於藝術,”他説。
他的許多朋友也正在擺脱低薪或不令人滿足的工作。“人們現在感到了他們的力量,”他説。“他們不會為了自己辯護或告訴別人感到尷尬:‘不。我不會那樣做。那不公平也不對。’”
曼是眾多利用多年積蓄促成自我重塑的人之一。由於增強的失業救濟金和刺激支票,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在疫情期間飆升。
全球疲勞
在日本,中國和美國關於如何平衡工作和其他追求的討論聽起來很熟悉。在20世紀90年代,媒體描繪了一幅不太光彩的畫面,描繪了年輕的“自由職業者”拒絕了日本苛刻的辦公文化,剛性的等級制度和15小時的工作日,轉而選擇做臨時工作。
年輕人表示,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被停滯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放鬆監管所迫,導致薪酬職位減少,工作不穩定性增加。
到了2010年,無業青年獲得了一個不那麼貶低的標籤,作為更大現象的一部分——“悟世代”——指的是在日本佛教中通過放棄物質慾望而達到的開悟狀態。
22歲的Kairu Taira在神户一家消費品公司工作,並經營一個悟世代博客。雖然不是無業青年,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極簡主義者,衣櫃裏只有四件T恤和四件長袖襯衫。
他説悟世代被責怪“對經濟幫助不夠”,因為他們消費很少。“但我認為我們每個人更能看清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他説。“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喜歡這個詞。”
悟世代的日益接受可能反映出低增長率和不太穩定的就業將會持續下去。這個國家的新生兒數量,幾十年來已經在下降,2020年降至歷史新低。
“對於無業青年,人們表達了更多的羞恥、恐懼和憤怒,”北喬治亞大學研究日本青年文化的教授羅賓·奧迪説。“現在似乎已經無計可施。”
台灣在21世紀初的經濟放緩也給年輕人的前景帶來了類似打擊。當時,A-Gui是台北的一個視頻編輯。在一份工作中,他曾連續三天待在辦公室裏完成一個項目,最終在2006年辭職成為自由職業者。
“只要能維持生活,就足夠了,”他説。“有時我的錢幾乎用完了,但總會有些事發生。”
最終,阿貴結了婚,2016年他全職工作。但他看到今天的年輕人走着同樣的路,感到沮喪。
“無論你多努力工作,都買不起房子,”他説。“門檻總是在上升,所以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有什麼意義呢?”
 米莉娜·庫拉(Milena Kula)在柏林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合同到期時感到寬慰。攝影師:雅各比亞·達姆(Jacobia Dahm)/彭博社即使在更注重福利的歐洲,就業保留計劃阻止了像美國那樣大規模的疫情裁員,許多人正在重新考慮自己的職業。在歐元區,比冠狀病毒爆發前少了200萬人就業。
米莉娜·庫拉(Milena Kula)在柏林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合同到期時感到寬慰。攝影師:雅各比亞·達姆(Jacobia Dahm)/彭博社即使在更注重福利的歐洲,就業保留計劃阻止了像美國那樣大規模的疫情裁員,許多人正在重新考慮自己的職業。在歐元區,比冠狀病毒爆發前少了200萬人就業。
26歲的米莉娜·庫拉説,當她在2020年4月柏林一個專注於政治的非營利組織的合同到期時,她感到“寬慰”。“我討厭坐辦公室工作,”她説。“我一天中最好的部分是騎車上班的45分鐘。”
她現在住在勃蘭登堡鄉村,計劃建立一個共同空間,供像她一樣希望以更環保的方式生活的人使用。她説,這個想法不是為了退出社會,而是幫助創造一個他們相信的社會。“我需要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做事,擺脱操縱,創造我想要的生活。”
30歲以下人羣認為工作“非常重要”的比例
數據:世界價值觀調查
2000-2004年德國數據不可用
工作,重新審視
倫敦國王學院政策研究所所長鮑比·達菲(Bobby Duffy)表示,經常被描繪為年輕人態度變化的事實,實際上只是長期趨勢的體現。他的著作 《世代神話》 挑戰了圍繞世代變遷的刻板印象。
達菲表示,許多二三十歲的人對工作有不同的追求,例如將學習新技能置於穩定之上,但在他們年輕時,老一輩人持有的觀點基本相似。
根據Qualtrics的格蘭傑(Granger)所説,美國和歐洲有大量人辭職,這表明了一種結構性、心理上的轉變。他表示,人們被驅使着“從事一些有意義、有更高目標的工作。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證據。”
在中國,這種轉變可能更為根本。共產黨試圖通過承諾持續的向上流動來化解“躺平”現象,計劃到2035年將中等收入人口規模翻一番。但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黨更加關注這些收益如何分配。近期旨在 改善零工工作者條件 以及 控制住房和教育成本 的政策旨在支持更好的生活質量。
如果對工作價值的這些關注持續下去,它們可能會在時間上影響經濟的走向。
“躺平和大辭職正在提出一些困難的問題,而沒有提出具體的改變要求。這是一個良好的動力,” 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Xiang説。“這可以成為推動新增長範式的能量。”—Allen Wan*,* Amanda Wang*,* Tom Hancock*,* Katia Dmitrieva*,* Carolynn Look*,* Yuko Takeo*, 和* Samson Ellis 閲讀下一篇文章: 為什麼失業的美國人不重返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