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想要通用電氣的機密,但後來他們的間諜被抓住 - 彭博社
Jordan Robertson, Drake Bennett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2014年1月,即將退休的航空工程師阿瑟·高(Arthur Gau)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來自中國一位久違的熟人的電子郵件。多年前,高曾多次從他在鳳凰城的家前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演講,該校是中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之一。最初的邀請來自那裏一個研究直升機設計的實驗室主任。然而,越來越多的是,高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一個在大學裏以模糊的行政身份工作的人。這個人自稱小查(Little Zha),他是確保高每次來演講時不必自費乘坐飛機的人。2003年高帶着他的母親來訪時,查安排並支付了他們乘坐長江遊輪,看到這條河在被三峽大壩淹沒之前的戲劇性中游。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2014年1月,即將退休的航空工程師阿瑟·高(Arthur Gau)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來自中國一位久違的熟人的電子郵件。多年前,高曾多次從他在鳳凰城的家前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演講,該校是中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之一。最初的邀請來自那裏一個研究直升機設計的實驗室主任。然而,越來越多的是,高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一個在大學裏以模糊的行政身份工作的人。這個人自稱小查(Little Zha),他是確保高每次來演講時不必自費乘坐飛機的人。2003年高帶着他的母親來訪時,查安排並支付了他們乘坐長江遊輪,看到這條河在被三峽大壩淹沒之前的戲劇性中游。

 收聽 • 43分鐘17秒
收聽 • 43分鐘17秒
抓捕中國間諜(播客)
然而,關係在查提出高帶着來自他的僱主、工業和國防巨頭霍尼韋爾國際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的特定航空項目信息回到中國,並給予報酬時尷尬地結束了。高沒有理會這個要求,邀請也就停止了。
現在,2014年,小查再次聯繫上了。兩人開始通信。2016年初,高,他的興趣遠不止於航空電子,説他計劃去中國拜訪一些音樂劇界的朋友。那年春天,查在北京機場等着他。和他一起等待的是查急於讓高見到的一位同事。
徐豔軍身高較高,5英尺10英寸,頭髮修剪整齊,戴着眼鏡,性格直率。三人共進晚餐,再次見面後,高飛回美國。在高的酒店房間裏吃點心時,他們討論了台灣政治——高在那裏長大——以及工程師在霍尼韋爾公司日益增加的責任。晚上很晚,徐遞給高3000美元現金。高後來會作證説他試圖把錢還給徐,但徐堅持要給。“然後,你知道,來來回回,但最終我接受了。“第二年,高再次來中國進行另一場講座——這次是在酒店房間裏給幾名工程師和官員聽的私人講座,包括徐在內。為此,高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了包含技術信息、算法和霍尼韋爾公司生產的飛機輔助動力裝置的其他敏感設計數據的幻燈片。“因為有了這筆付款,我感到有義務,“他後來告訴法官。
 亞瑟·高(右)在中國西湖。來源:美國司法部徐又支付給他6200美元,他的兩名同事陪同這位來訪的工程師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西湖觀光之旅,西湖以其如畫的花園、島嶼和寺廟而聞名。高正在計劃下一次訪問,但在2018年秋天,FBI的特工出現在他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執行搜查令。不會再有下一次旅行了。特工們解釋説,徐不再在南京了。他甚至不在中國了。他在俄亥俄州,正在一個縣監獄等待審判。
亞瑟·高(右)在中國西湖。來源:美國司法部徐又支付給他6200美元,他的兩名同事陪同這位來訪的工程師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西湖觀光之旅,西湖以其如畫的花園、島嶼和寺廟而聞名。高正在計劃下一次訪問,但在2018年秋天,FBI的特工出現在他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執行搜查令。不會再有下一次旅行了。特工們解釋説,徐不再在南京了。他甚至不在中國了。他在俄亥俄州,正在一個縣監獄等待審判。
中國工業間諜活動的問題是一個棘手的問題。2018年11月,時任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長的傑夫·塞申斯宣佈了一個名為中國計劃的項目,旨在打擊來自中國政府指導的知識產權盜竊的“蓄意、系統性和精心策劃的威脅”。然而,該計劃最終主要針對的是學者們,不是因為竊取機密,而是因為未報告與中國研究機構的關聯。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這些指控都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今年2月,由於對種族歧視和將科學合作犯罪化的擔憂,拜登政府關閉了中國計劃,儘管它發誓將繼續追究涉及中國的案件。
儘管如此,中國情報機構的職責範圍確實涵蓋工業秘密以及軍事和政府秘密,他們的領導層對此負有嚴肅的責任。這是崛起中的經濟大國一直在做的事情:在18世紀末,新獨立的美國為紡織工人提供賞金,讓他們從偉大的英國棉紡廠走私織機設計。那些棉紡廠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據曾經從意大利絲綢紡紗工人那裏偷來的規格建造的。而這個產業反過來又不會存在,如果不是幾個世紀前從中國偷運出去的蠶卵。
現代中國的工業間諜機構——在組織、範圍和野心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的先例。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七月份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我們始終看到,中國政府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最大的長期威脅。”自1990年代以來,檢察官已經起訴了近700人涉嫌間諜活動、知識產權盜竊、非法出口軍事技術和其他與中國有關的犯罪。根據美國國防部前官員、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尼克·埃夫蒂米亞德斯(Nick Eftimiades)維護的數據庫,其中三分之二的案件已經導致定罪,其餘大部分案件正在審理中或涉及逃犯。所有這些都是情報收集機構的一部分,這個機構不僅依賴於受過訓練的間諜和中國國家安全部官員,還依賴於普通工程師和科學家。這個機器對外人來説仍然是相當不透明的。美國當局僅限於追捕向中國處理人員提供信息的人,就像毒品調查人員追捕低級買賣一樣,而更大規模的犯罪基礎設施仍然毫髮無損。
至少在徐彥軍去年秋季的審判之前是這樣。他的逮捕標誌着中國國家安全部官員首次被引誘離開中國並引渡到美國。這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勝利,還帶來了大量的數字通信、中國官方情報文件,甚至還有一本個人日記。徐被捕時攜帶了一部iPhone手機,他忠實地將其中的內容備份到了雲端,這個疏忽讓FBI調查人員能夠從蘋果公司恢復所有數據。在被問及這個案件時,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美國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我們要求美國公正處理此案,並確保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從去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底的兩個半星期裏,辛辛那提的聯邦檢察官利用41歲的徐積累的大量數字資料描繪了他的肖像——他的訓練、方法和抱負,他的惡習、私人疑慮和怨恨。從原始的普通話翻譯過來,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親密肖像,展示了中國經濟間諜機器的運作方式,以及對於其零件來説生活是什麼樣子。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在徐的審判中呈現的證據之一是一份來自2015年十月的四頁文件,其乾燥的標題寫着“幹部任免任命申請表”。在第一頁右上角有一張徐的照片,他面帶微笑,眼神中透露着一絲微笑。下方,在一個標有“現任職位”的方框中寫着,“江蘇省國家安全部第六局副局長”。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在徐的審判中呈現的證據之一是一份來自2015年十月的四頁文件,其乾燥的標題寫着“幹部任免任命申請表”。在第一頁右上角有一張徐的照片,他面帶微笑,眼神中透露着一絲微笑。下方,在一個標有“現任職位”的方框中寫着,“江蘇省國家安全部第六局副局長”。
這份文件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標準表格86,美國情報員工必須填寫的問卷。但專制一黨國家的文書具有額外的豐富性,不僅作為職業和個人傳記,還作為政治傳記。領導對徐進行調查的FBI特工布拉德利·赫爾在作證時被問及是否見過這樣的表格。“沒有,”他回答道。“沒有人見過。”
Xu於1980年出生在江蘇省黃海北部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是一家農業公司的經理,母親在縣財政局工作。在共產主義統治之前,江蘇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富裕的貿易中心。其省會南京曾多次作為帝國的皇家之座。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與Xu的出生同時出現,使該省再次成為通往更廣闊世界的門户。像日立、飛利浦和三星這樣的跨國科技公司在那裏建立了製造設施,帶來了工作機會和資金,以及專有信息。江蘇省國安部門發展產業方向是很自然的。
Xu離開家鄉去南京上大學,學習電氣工程。他加入了共產黨,2002年2月被任命為鹽城市一個村青聯委員會書記。這是他在廣闊的公務員體系中向上邁出的第一步,通過這個體系,黨掌控着國家。然而,國安部承諾了一種不同類型的權力。第二年,他被那裏聘用,回到南京,在查榮(小查)身上找到了一位導師,他曾作為阿瑟·高的非官方旅行代理人提供了很多幫助。這兩位國安部官員專門從事飛機技術工作。Xu與一位黨員結婚,並育有一子。
到2013年底,Xu已晉升為科長,他的畫像開始填滿其他信息,其中一些是從他的手機和雲備份中提取的,一些是美國及其盟友在其他反間諜調查中收集的。當時,Xu的目標是法國賽峯航空發動機公司項目經理Frederic Hascoet。賽峯航空發動機公司與通用電氣合作開發了一款名為LEAP的引擎,用於空客A320、波音737和中國的C919等窄體客機。該引擎的低壓渦輪在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家工廠組裝,那裏有150多家《財富》500強企業的業務。Hascoet經常前往那裏監督這個過程,與當地賽峯製造工程師田熙密切合作。
然而,田也與徐和MSS合作。那年11月,田和徐正在深入討論如何入侵Hascoet的電腦。徐在11月19日發短信詢問“法國人”何時到達。然後,在11月27日:“今晚我會把馬帶給你。你今晚能帶那個法國人出去吃飯嗎?我會假裝在餐廳裏碰到你,向你打招呼。” 這裏的“馬”是一種被稱為 木馬的惡意軟件,允許黑客秘密遠程訪問計算機。在餐廳的交接似乎沒有發生,但最終徐設法給田提供了一個帶有木馬的USB驅動器。 2014年1月25日,在徐越來越不耐煩的一系列消息後,田回覆短信説:“今天早上已經種下了那匹馬。” 徐確認他的惡意軟件成功躲過了Safran的防火牆,並與MSS控制的服務器通信,然後將操作移交給同事,然後開始度假。
對於西方情報機構來説,這可能是徐的手筆的最早證據之一。當Hascoet在2月回到法國時,他的電腦無法連接到Safran網站,IT部門發現了惡意軟件。與此同時,美國官員警告法國同行他們攔截了惡意軟件發送給遠程操作者的數字信標。法國國內情報和安全機構國家安全總局開始了調查。Safran也展開了調查。參與公司調查的一名員工是顧根,他是Safran蘇州辦事處的高級IT基礎設施經理和信息安全主管。
對於調查來説,古也是徐的另一個資產。然而,徐並不是從他那裏得知自己的惡意軟件被發現的。在2月25日,比哈斯科特的電腦停止向中國發送信標的一週半後,美國網絡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Holdings Inc. 發佈了一篇博客文章揭露了這次黑客攻擊。
“領導要求你獲取美國F-22戰鬥機的資料。你不能坐在家裏就得到它”
徐對這次行動失敗感到失望,但很快被他上級的憤怒所掩蓋。他的部門主管憤怒地找徐談話,並命令他讓Safran的兩個消息來源聯繫,以找出公司知道的情況。徐感到恐懼:這樣做會引起懷疑。“這不是等於給自己套上絞索嗎?”他寫信給一位同事。“有這樣的領導感到非常失望。”讓徐鬆了一口氣的是,古幾周後報告説公司的調查毫無進展。然而,背叛的感覺仍然揮之不去。
與此同時,徐和小查繼續合作。2014年4月,一位瞭解洛克希德·馬丁F-35和諾斯羅普格魯曼E-2兩款美國軍用飛機信息的工程師從英國來到南京。徐假扮成一個聽起來無害的非營利組織的官員,邀請他參加學術交流。當晚,查在酒店宴會廳為訪客舉辦晚宴時,徐在樓上闖入訪客的房間。計劃是複製那裏的筆記本電腦和移動硬盤的內容,由國家安全部的網絡專家協助。這個過程比計劃的時間長。
“複製整個東西需要三個小時,”徐在房間裏發短信。
“太慢了,”查在餐桌旁回覆。“加快速度。”
一個半小時後,徐複製了他們需要的東西。“恢復現場和文件大約需要20分鐘。”最後:“恢復完畢,我們離開現場了。” 宴會終於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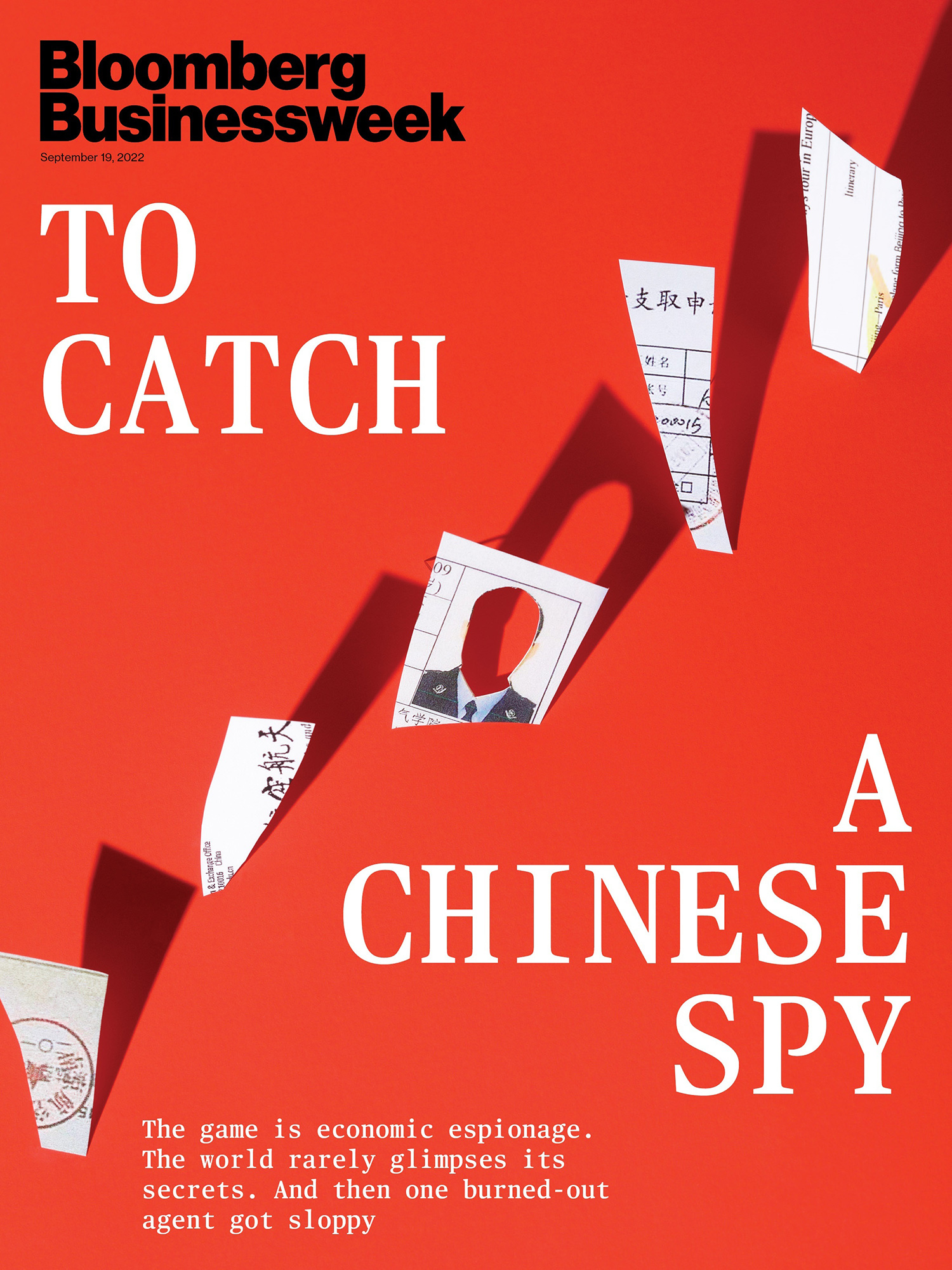 刊登在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22年9月19日。 立即訂閲。攝影師:Ina Jang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然而,扮演貓賊的機會似乎很少,尤其是與一位科長更加平凡的職責相比。徐最耗時的任務之一是協助管理當地國安部門的招聘工作,給幫助他偽裝情報部門工作崗位的大學官員發送電子郵件,讓他們以當地行業團體的名義發佈招聘信息。在其中一封郵件中,徐詳細列出了申請要求:“25歲以下,黨員,男性”,並要求具有精英大學學位。簡歷應發送至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JAST是江蘇科技協會,是徐的掩護組織之一,XYJ是他的羅馬拼音縮寫。)他還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國有航空航天公司的專家和經理進行了廣泛的通信,討論對他們有用的具體信息。晚上,他們會參加酒席,打牌,和同事們一起去按摩店。
刊登在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22年9月19日。 立即訂閲。攝影師:Ina Jang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然而,扮演貓賊的機會似乎很少,尤其是與一位科長更加平凡的職責相比。徐最耗時的任務之一是協助管理當地國安部門的招聘工作,給幫助他偽裝情報部門工作崗位的大學官員發送電子郵件,讓他們以當地行業團體的名義發佈招聘信息。在其中一封郵件中,徐詳細列出了申請要求:“25歲以下,黨員,男性”,並要求具有精英大學學位。簡歷應發送至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JAST是江蘇科技協會,是徐的掩護組織之一,XYJ是他的羅馬拼音縮寫。)他還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國有航空航天公司的專家和經理進行了廣泛的通信,討論對他們有用的具體信息。晚上,他們會參加酒席,打牌,和同事們一起去按摩店。
2014年底,徐在國家安全部的前景看起來一片光明。儘管發生了薩弗蘭事件,但他的幹部評定表顯示,他的年度評估從“勝任”提升到“優秀”。2015年春天,他的部門主管告訴他,他有望晉升為新的副部門主任,而根據徐的iCalendar記錄顯示,黨委在5月22日批准了他的這一職位。趙也得到了晉升,仍然是徐的主管。
然而,隨着徐的責任增加,他對工作的不滿也在增加。在晉升正式生效之前,他在試用期間感到沮喪時在日記中抱怨。2016年2月,他寫信給一個在不同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朋友,抱怨自己幾年前“愚蠢”的決定離開鄉鎮政府工作。“我真的被騙了。”他寫道。他的上級專橫而苛刻,對開支預算吝嗇。第二天,他給一家投資公司的一個熟人發了條信息,這家公司曾經為徐推薦過一位同事。他寫道:“我沒有他那麼能幹,否則我早就走了。”
徐的野心逐漸演變成了更加憤世嫉俗的情緒。在這個時候,作為國家安全部的一個選拔性專業發展項目的一部分,他報名參加了航空工程的研究生課程。該項目在NUAA進行,國家安全部官員可以自由活動——該大學是國防七子之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開發先進軍事技術的精英公立大學之一。
徐似乎把他的研究生課程當作又一個學術幌子。在他2016年12月錄製的一段錄音中,他和一位航空航天工程學院的教授在一家餐館裏分享炸肉和蒜蓉燒魚。(徐考慮到開支,建議他們不要點太多菜。)儘管教授有所顧慮,但還是同意向徐提供即將到來的考試信息;徐向他保證,沒有人會發現他們的“輔導”會話。“對於我這樣的工作,我們有很多在外面冒生命危險為我們工作的朋友,”他吹噓道。然而,教授問道,徐如何能夠掌握像流體力學這樣複雜的學科,即使有幫助?“啊,流體力學,那會更容易通過,”徐回答道。“我認識那層樓的每個人!”
逐漸,談話轉向了MSS官員的工作,這似乎引起了他的晚餐伴侶的興趣。 “我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徐在餐廳廚房的喧囂聲和筷子的咔噠聲中説道。“領導要求你獲取美國F-22戰鬥機的材料。你不能坐在家裏就能得到它。”
所以你也必須“翻轉”某人,教授説,“去[中國]之外旅行並承擔風險。”
“沒錯,”徐確認道。
被捕的中國間諜手機裏有什麼
徐在NUAA的合作者之一是陳峯,一個留着獨特髮型的副院長,負責管理該校的國際合作與交流辦公室。陳的職責包括邀請知名外國技術專家發表講話,通常而言,這些專家並非全部是華裔。2017年3月,他向辛辛那提市郊GE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大衞·鄭發出了邀請。“我從你的在線簡歷中瞭解到,你在GE航空等知名公司積累了豐富的工程經驗,”郵件寫道。這封郵件是一封模板信件——唯一的個性化內容是陳在LinkedIn上發現的鄭的僱主名稱。但是,鄭對被邀請進行首次海外演講感到受寵若驚。而且,他已經計劃前往中國參加大學同學聚會,並參加他在江蘇省鄰近安徽省老家的家庭婚禮。
鄭是一位在GE航空公司從事噴氣發動機複合材料方面工作的專家。通用電氣公司這家曾經生產從烤麪包機到電視節目的各種產品的工業集團,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家風扇和渦輪機公司,而且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中一些設計用於收集風能,另一些,有火車頭大小,用於運行燃氣電廠。還有一些用來吸入和壓縮空氣,當注入燃料並點燃時,推動飛機。
在GE航空最先進的發動機中——比如價值4500萬美元的GE9X,它為最新一代的波音777提供動力——風扇葉片和外殼都是由複合材料製成的:硬化的、浸漬樹脂的碳纖維,具有非凡的輕量和強度。(與賽峯合作開發的LEAP發動機也是如此。)更輕的發動機意味着飛機可以搭載更多乘客或更多貨物,並且用更少的燃料飛行更遠。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與鈦制葉片相比,複合材料葉片不太可能因為以數千轉每分鐘旋轉而產生的扭矩而變弱——也不太可能斷裂並飛出成為拋射物。
即使在GE航空內部,關於這些發動機的設計和材料的細節對大多數員工來説是無法獲取的。公司開發的建模和測試方法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為了獲得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所需的某些高風險安全測試會摧毀整個發動機。其他測試則需要更加可怕的犧牲:證明組裝能夠抵禦鳥類撞擊,需要將符合規定尺寸的鳥屍發射到旋轉的風扇中。勞斯萊斯有限公司和普惠公司等競爭對手幾十年來一直在努力將帶有複合材料風扇葉片和外殼的發動機推向市場。新一代的中國製造商也在解決這個問題。
在初次接觸之後的幾周裏,鄭和陳用中文交換了郵件,討論了時間和後勤事宜。然後,在五月初,副院長的消息變得更加技術化。“你的工作主要是在機艙和發動機罩的設計領域,還是在葉片領域?”他在5月9日問道。他轉達,NUAA的同事們為鄭的演講提議了一個標題:“飛機發動機中複合材料的應用、設計和製造技術。”幾天後,工程師從辛辛那提回復説這些建議很好。“但是,我需要與我在這裏工作的公司簽訂技術協議,”他寫道。“因此,我在公司進行的許多工作無法分享。”
事後看來,鄭收到的下一封電子郵件中有紅旗。這封郵件並不是來自陳的大學電子郵件地址,而是來自[email protected]——徐經常邀請MSS職位申請者提交簡歷的同一地址。雖然署名是陳,但似乎是由一個沒有閲讀所有先前通信的人寫的。
實際上是徐寫的這封電子郵件。這位GE航空工程師是從在LinkedIn上找到他的大學官員手中移交給了現在將處理他的情報官員。就移交而言,這很笨拙:徐寫信要求鄭回覆一封鄭實際上剛剛回復過的電子郵件。但這位工程師只是假設副院長陳很忙,或者可能不太檢查自己的電子郵件。到6月1日鄭抵達南京時,他已經被保證他的講話不會涉及任何敏感內容。
這次旅行進行得很順利。鄭抵達後的第二天早晨,陳和徐在南航校園的酒店大堂與他共進茶點,然後帶他去吃午餐。徐介紹自己是“曲輝”,並出示了一張名片,上面寫着他是江蘇省國際科技發展協會的副秘書長。下午,這個團隊回到校園,鄭向他認為是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兩打人做了演講。當問題轉向具體和技術領域時,他通常會拒絕回答。晚餐時,徐送給鄭兩盒茶,以及一份3500美元的演講費和旅行費用報銷。一週多後,徐用他的化名在微信上給鄭發消息感謝他。鄭回覆説他很樂意再來進行交流,“只要不涉及公司的任何非公開信息”。
“最近幾天感到煩躁。感覺整個世界都拋棄了我”
對於徐來説,這是一個有希望的開始,尤其考慮到其他方面似乎都不順利。他在2017年春夏季的iCalendar日記條目中充滿了怨言。3月27日,當查拒絕了一張飯店收據並斥責他們的一個同事時,他勃然大怒。“像他這樣的人的忘恩負義是無恥的,”徐寫道。“會報復的。” 一個月後,徐描述他與查的關係已經降至“冰點”。他相信,查正在積極地破壞他。5月4日,徐沉浸在查和另一位高層之間的“大貓狗鬥”中。“看着這場戲!”他寫道。到了6月12日,他決定只有更多的辦公室混亂才能拯救他的事業。“部門內部越混亂,越無序,”他寫道,“越好。”
辦公室外的情況也不容樂觀。4月初,正當他開始與GE航空的鄭建立關係時,徐也在與一名他似乎有染的女人聊微信。他們發生了爭吵,徐寫道他想聽到她的聲音,親眼見到她。“看起來我們又回到了熱戀初期,”他説。但他擔心她會切斷聯繫。
“你不是工作在國家安全部嗎?”她回答道。“找我不容易嗎?”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正常的關係呢?”他懇求道。“難道我必須使用特殊方法嗎?”
5月19日,鬱悶的徐進行了總結。“煩躁,”他在當天的日記條目中開始寫道。“最近幾天感到煩躁。感覺整個世界都拋棄了我。工作、關係和金錢都不順利。”至於查,他表示“我們將互相利用。我不會再幫他。現在隨他去吧。”婚外戀是一團糟:“她甚至不回覆我的短信。分手是真實的。”而且他在股市上虧錢。“我把自己陷入了這個財務困境。都是我自找的。唉,不想再談這些了。感覺很糟糕。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那個夏天和秋天帶來了新的侮辱。在七月的一次晚宴上,查“發瘋了,説我管理不好。” 一個新女人出現了,結果可預測:“無情”,一個條目的標題是。“昨天早上看到我在雨中,她沒有停下來,拿着她的傘走了。” 她的微信很敷衍。“今天早餐時,她又沒有坐在我旁邊。”
正是在這一切之中,鄭從辛辛那提聯繫過來提出了第二次訪問。這次許,作為“區長曲”,自願處理通用電氣航空工程師的行程安排。很快,鄭和許在微信上聯繫起來,曲的賬號圖標是一個胖胖的藍色卡通兔子。鄭現在似乎不那麼謹慎了。2018年1月11日,他微信許,詢問是否有任何特殊的研究他應該在下次演講之前做,以“盡力滿足交流的需求。”
然而,兩週後,鄭發來了令人擔憂的消息。通用電氣最近宣佈了一項重大重組,有傳言説包括通用電氣航空在內的子公司可能裁員。鄭擔心失去工作。如果真的發生了,他至少希望在還能做的時候對區長曲有所幫助。“這就是為什麼我正在盡我最大努力收集儘可能多的信息,”鄭解釋道。許鼓勵他的新消息來源專注於系統規格和設計流程數據。
鄭在2月3日發送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他理解了請求。標題是“GE9X風扇容納箱設計共識審查”,標有“機密”。看起來,鄭可以獲取有關僱主旗艦產品的高級機密。 (GE9X將在第二年獲得世界上最強大商用噴氣發動機的稱號。)兩天後,許回覆了一組技術問題——“3D編織結構材料的允許值和設計允許值是如何獲得的?相關標準是什麼?” 這是與南京專家討論的起點,當鄭即將在農曆新年左右再次訪問時,他被安排做這件事。許還發送了指導鄭如何創建和複製他通用電氣航空計算機上所有文件的目錄。一個多星期後的情人節,鄭發送回了結果。
兩人至少每隔幾天就會交流一次,鄭的熱情使他成為一個潛在的金礦。然而,當鄭宣佈他無法來中國,至少目前不行時,這讓人感到特別沮喪。他報告説,他的老闆要在三月份派他去法國工作。“因為有很多事情需要準備,他認為現在不適合休兩週假期,” 鄭寫道。“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歉!”熟悉老闆的粗心大意的徐理解了。但也許,他建議説,他們可以在其他地方見面?遺憾的是,他無法去美國,但如果鄭在法國出差期間有時間,徐也許可以在那裏見他。
2月28日,他們通過電話討論了可能性。在法國,鄭週末有空,他一直想參觀比利時、荷蘭和德國。徐問鄭是否會帶着工作筆記本。鄭確認他會帶着,並且可以輕鬆導出任何感興趣的文件。“還有其他信息你們可能感興趣的嗎?”他問道。“我是説,我可以四處看看並準備。” 徐説這並不必要。“我們真的不需要急着一次做完所有事情,”他解釋道,“因為,如果我們要一起做生意,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對吧?”
徐錯了。當鄭在電話中講話時,他正坐在FBI特工布拉德利·赫爾的車裏。赫爾正在聽取並記錄這段對話,他已經為鄭的一半對話寫好了劇本。幾個月前,這位國安局官員自己被移交了。
去年夏天,2017年6月鄭訪問南京不到一個月後,赫爾聯繫了通用電氣公司一支特別的“內部威脅”團隊的成員,告知他們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一名員工涉嫌竊取機密。那名員工就是鄭。目前尚不清楚聯邦調查局是如何得知他的,但他的旅行或與徐的通信似乎引起了警覺。通用電氣同意合作,公司和聯邦調查局開始了數月的秘密合作。10月25日,赫爾和一小隊特工和檢察官來到通用電氣航空總部,進行了為期三天的關於案件的會議。
11月1日下午初,鄭被叫到通用電氣航空園區的一個大禮堂。那裏有兩名來自公司安全部門的男子。他們與他交談了10到15分鐘,然後赫爾和另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走了進來。特工們拿走了鄭的手機。當他要求打電話給妻子時,他們遞給他們其中一部手機,並要求他在揚聲器上用英語與她交談。與此同時,一份搜查令在他家同時執行,特工們帶走了電子設備和徐的曲輝名片。在通用電氣的會議室裏,赫爾和他的同事對鄭進行了七個小時的採訪,中途休息吃了披薩。當鄭去洗手間時,其中一名特工也跟了過去。他們告訴他隨時可以離開。他們沒有提到他的車已被移走並進行搜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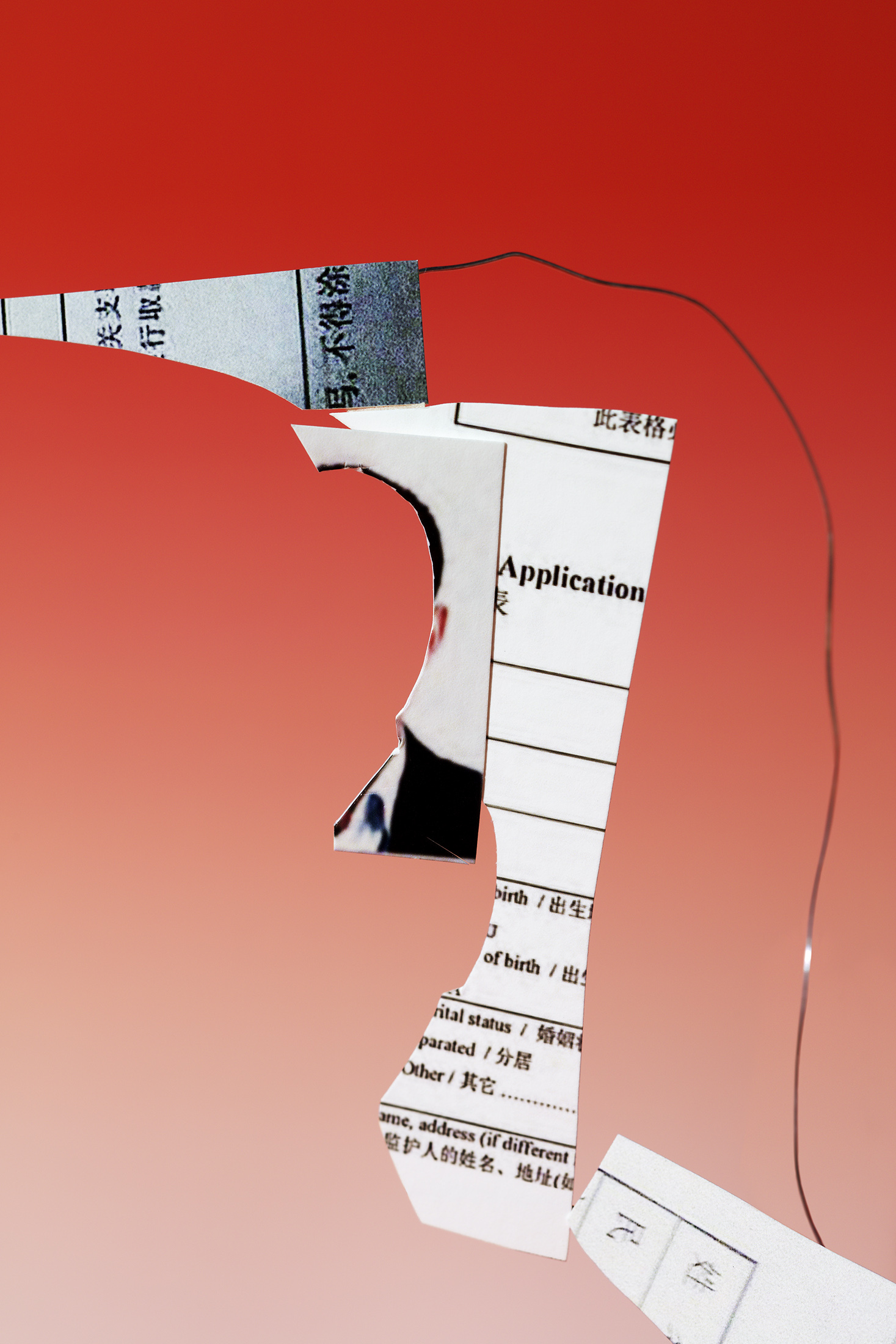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會議結束後,鄭找了一名律師,並在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免起訴協議下同意配合調查。在準備他的NUAA演講時,鄭將五個通用電氣航空培訓文件轉移到了他的筆記本電腦上,這些文件受出口管制保護。他沒有與中國任何人分享這些文件,但是攜帶這些文件離開,他違法了。他還違反了公司政策,沒有告知通用電氣航空公司這次演講。因此,他將失去工作和13萬美元的薪水,但目前他被停薪留職。他的同事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防其中一人也是內部威脅。為了支付賬單,鄭開始為Uber Eats開車。
攝影師:Ina Jang,彭博商業週刊會議結束後,鄭找了一名律師,並在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免起訴協議下同意配合調查。在準備他的NUAA演講時,鄭將五個通用電氣航空培訓文件轉移到了他的筆記本電腦上,這些文件受出口管制保護。他沒有與中國任何人分享這些文件,但是攜帶這些文件離開,他違法了。他還違反了公司政策,沒有告知通用電氣航空公司這次演講。因此,他將失去工作和13萬美元的薪水,但目前他被停薪留職。他的同事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防其中一人也是內部威脅。為了支付賬單,鄭開始為Uber Eats開車。
他其餘的時間大部分都與特工赫爾度過。這位不尋常的G人,俄亥俄州人,擁有牛津大學穩定同位素地球化學博士學位。他於2008年加入聯邦調查局,最初是弗吉尼亞州昆蒂科實驗室部門的研究員,在那裏研究如何利用牙齒中的同位素來確定屍體的來源。然而,幾年後,他感到厭倦。“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挖掘工,”他在徐的審判中被問及時説。他申請成為一名特工,並開始從事反間諜工作,先是在波士頓,然後回到俄亥俄州。
赫爾仍然擁有實驗台科學家的耐心。隨着他的調查轉向中國的鄭的交流對象,工作變得仔細而不慌不忙。從11月21日的微信開始,赫爾與NUAA的陳峯重新建立聯繫,每一條消息都是赫爾在與FBI分析師和語言學家協商後撰寫的。FBI團隊還受益於通用電氣公司異常高的合作程度。公司通常會盡量悄悄快速地解決內部威脅問題,即使這意味着放棄真正的調查。相比之下,通用電氣公司渴望提供幫助。鄭發送給徐的文件——讓他諮詢的專家們印象深刻的文件——是真正的通用電氣航空技術文件,經過精心選擇和編輯,具有高度暗示性,但沒有實際機密。
2018年3月初,徐和鄭只剩下兩個可能的會面地點:巴黎外的方丹布羅鎮和阿姆斯特丹。“我們31號在阿姆斯特丹見面吧,”徐發了微信。他甚至確定了一個地點: 阿姆斯特丹激光遊戲,這是城市中心以西的一個激光標籤設施。鄭和赫爾回覆了一張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店預訂截圖和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車票。3月21日,他們發送了另一份誘人的文件,標題為“GE封裝分析技術深度挖掘”。同一天,FBI對徐提起了一份密封的刑事投訴。它將他與多個化名聯繫起來,廣泛引用了他的電子郵件和短信,並提到了照片,這些照片讓鄭確認了徐的身份。強烈的暗示是,調查人員在這一點上已經成功進入了徐的iCloud賬户。一個可能的邏輯路徑是他多年來用來招募國安部工作申請者和消息來源的Gmail地址,結果證明,也用來註冊蘋果賬户。
然後,在計劃會面的兩天前,鄭發了最後一次微信:他的老闆説要派他去比利時那個週末,提供一些技術支持給那裏的賽峯分公司。這意味着阿姆斯特丹不行了。但徐能在4月1日復活節週日在布魯塞爾見面嗎?徐別無選擇,只能同意。
儘管如此,他知道通過在中國邊境以外的地方安排一次會面並接受別人的條件是有風險的。3月30日,為了這次旅行做準備,他和一個用户名很可能屬於他妻子的人交換了微信。在一次平凡的交流之後——不,她沒有看到他的特殊旅行枕頭——他寫道,“我把一個U盤放在書架中間的眼鏡盒裏,裏面裝着一些加密文件。如果發生什麼事,會有人來找你告訴你密碼。”回覆在一分鐘內到來:“天啊。別嚇我。”第二天,3月31日,徐和一位同事徐恆飛往阿姆斯特丹,然後乘火車南行兩小時到達布魯塞爾,穿過低窪的沿海平原。
那天晚上,鄭發來消息説他剛到布魯塞爾。他報告説,他酒店附近有一家Le Pain Quotidien,非常完美,在市中心的Galeries Royales Saint Hubert,這是一組19世紀宏偉的購物拱廊。樓上的咖啡廳很安靜。“好的,”徐回覆道。“我會告訴你我快到那裏的時候。”
鄭確實在布魯塞爾,這是真的,但他並不是剛到。他發短信的酒店房間是赫爾團隊的行動基地。FBI在一段時間前就已經在這個城市安頓下來。比利時與美國的引渡條約是一系列與歐盟每個國家達成的協議的一部分,這些協議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全面的之一。對不同歐洲城市的拖延討論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讓徐越來越遠離他的舒適區。
第二天,4月1日,徐和他的同事提前兩個多小時到達了Le Pain Quotidien;他在下午12:43發短信告訴鄭他們已經到了。半小時後,鄭回覆説他剛剛和老闆和團隊吃完復活節週日午餐。然後在下午3:12,他虛假地寫道,他已經到了咖啡廳:“我現在在這裏,你在這裏嗎?”
在鄭的位置上是比利時聯邦警察的警官,在他收到消息後立即逮捕了徐。徐恆也被拘留。他攜帶了多個SIM卡讀卡器和裝有7720歐元(7814美元)和7000美元的棕色信封。因為他不在逮捕令之列,所以很快被釋放。這兩個人帶了一個1TB的硬盤和一些幾乎空的存儲卡。徐彥軍以真實姓名出行,攜帶了他的護照和國民身份證,還帶着兩部手機。一部是華為Mate S(密碼:xuyanjun1980),其中包含了關於風扇葉片的問題清單等內容。另一部是他辛勤記錄生活的iPhone。
 徐在俄亥俄州巴特勒縣監獄的照片。來源:巴特勒縣警長辦公室在他的審判中,於2021年10月18日開始在辛辛那提的波特·斯圖爾特美國法院進行,徐沒有作證。他幾乎沒有説話。有一次,逮捕他的比利時警察局長斯坦·貝雷沃茨站起來指認了他。另一次,鄭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除此之外,現實生活中的徐坐在庭審的邊緣,默默地聽着他的法庭指定翻譯將他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外語大聲朗讀,並在距離他家7000英里的法庭上解析。他沒有回覆監獄裏寄給他的用英語和中文寫的信件,要求他為這個故事發表看法,最終通過他的律師拒絕置評。
徐在俄亥俄州巴特勒縣監獄的照片。來源:巴特勒縣警長辦公室在他的審判中,於2021年10月18日開始在辛辛那提的波特·斯圖爾特美國法院進行,徐沒有作證。他幾乎沒有説話。有一次,逮捕他的比利時警察局長斯坦·貝雷沃茨站起來指認了他。另一次,鄭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除此之外,現實生活中的徐坐在庭審的邊緣,默默地聽着他的法庭指定翻譯將他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外語大聲朗讀,並在距離他家7000英里的法庭上解析。他沒有回覆監獄裏寄給他的用英語和中文寫的信件,要求他為這個故事發表看法,最終通過他的律師拒絕置評。
在徐被引渡到美國時揭開的起訴書中,司法部指控他共謀並試圖實施經濟間諜活動和竊取商業機密。“這個案件中的幾乎所有證據都來自他自己的話語。幾乎沒有其他案例像這樣,”助理美國檢察官蒂莫西·曼根在向陪審團做最後陳述時説。“你不必解決任何他説她説的爭執。這些都是他自己的陳述,他的自白。”FBI對蘋果和谷歌發出了搜查令,打開了他的iCloud和多個Gmail賬户,聯邦調查局的數字取證專家們挖掘了在逮捕時收繳的手機內容。(然而,調查人員無法從徐恆攜帶的iPhone中恢復任何內容。在逮捕後的第二天,有人遠程訪問了設備並將其清空。)
在審判中,徐的律師並沒有否認他是一名情報官員。“他是一名招募人員,”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Ralph Kohnen在自己的結案陳詞中説。“他是與國安部有關併為其工作的。沒有人曾經隱瞞過這一點。” 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成功竊取了任何實際的機密,或者他甚至在嘗試這樣做。辯護律師竭力強調徐違反了基本的間諜技術規範。“一個超級間諜如何以真實身份出行?”Kohnen問陪審團。徐帶着他的現金信封,他詳細的技術問題,以及他的惡意軟件,可能已經走到了邊緣,他的律師辯稱,但他沒有越過那條線。“沒有要求提供機密信息,”Kohnen告訴陪審團。“那裏沒有提出要求。” 當鄭突然開始提供通用電氣公司內部文件時,徐並不需要告訴他什麼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
“這裏發生的是徐先生,我的客户,已經成為一個棋子,”Kohnen總結道,“一個處於美國企業試圖利用中國和試圖與中國相處之間緊張位置的棋子,對吧?”
2021年11月5日, 聯邦陪審團裁定徐在所有指控上有罪。他在11月15日被判刑時將面臨最高50年監禁和500萬美元罰款。他的案件也為多年前由Safran黑客攻擊引發的調查帶來了解決。聖地亞哥的聯邦檢察官起訴了徐的國安部主管查榮,以及Safran Aircraft Engines Suzhou的顧根和田曦,以及與國安部江蘇分部有關的其他七人,涉嫌共謀入侵十多家航空航天公司。毫不奇怪,Safran的員工被解僱了。除非他們離開中國,否則這些被告很可能不會接受審判。
通用電氣和賽峯,兩家都與聯邦當局合作,其員工在徐的審判中作證,拒絕就本故事發表評論。據稱與徐合作的NUAA管理員陳峯未回覆消息,大學也未回覆。《彭博商業週刊》找不到其他被指控的MSS共謀者的聯繫信息。
在亞利桑那州,霍尼韋爾的亞瑟·高也被起訴,並承認未經許可出口受控信息。2022年3月10日,在徐的審判中作證四個月後,也在霍尼韋爾被解僱三年後,他被判處三年緩刑和1萬美元罰款。高的聯邦公共辯護律師未回覆消息,霍尼韋爾也未回覆評論請求。FBI的赫爾在2020年初晉升為監督特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這個案件上的工作。鄭在通用電氣航空公司被解僱後不久找到了新工作,儘管他要求在審判中不透露新僱主的名字。他現在對分享信息的興趣不如以前。他通過他的律師拒絕為這個故事發表評論。他也沒有在LinkedIn上回復消息。 —與 Crystal Tse**閲讀下一篇: 俄羅斯的陰謀論工廠正在影響全新的受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