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完全拋棄“土地財政”可能帶來哪些風險?
上篇請點擊:《趙燕菁:“土地財政”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礎》
【文/趙燕菁】
“土地財政”的問題與風險
“土地財政”的問題
同任何發展模式一樣,“土地財政”雖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好處,但也引發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很可能會給整個經濟帶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Lewis,1978)就發現,城市人口每年增長率超過3%的國家大多資本短缺,需要向城市人口增長率低於3%的國家借貸。其後果,不會小於税收財政帶來的“大蕭條”“金融風暴”“主權債務危機”。
第一,“土地財政”必定使得不動產變成投資品。
“土地財政”的本質是融資,這就決定了土地乃至為土地定價的住宅必定是投資品。買汽車公司股票的人,並不一定是因為沒有汽車。同樣,買商品房(“城市股票”)的人,也並非一定因為沒有住房。只要存在“土地財政”,不動產就不可避免地會是一種投資品。無論怎樣打壓住房市場,只要不動產的收益和流動性高於股票、黃金、儲蓄、外匯等常規的資本貯存形態,資金就會持續流入住房市場。
第二,拉大貧富差距。
“土地財政”不僅給地方政府帶來巨大財富,同時也給企業和個人快速積累財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資不動產在一代人之內完成數代人都不敢想的鉅額財富積累,成為過去十餘年的註腳。但與此同時,沒有機會投資城市不動產的居民與早期投資城市不動產的居民的貧富差距迅速拉開。房價上漲越快,貧富差距越大。房地產如同股票,會自動分配社會增量財富。正是這一功能,阻礙了不同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的渠道。
第三,佔用大量資源。
如果説中國經濟“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房地產市場首當其衝。同虛擬的股票甚至貴金屬不同,以不動產為信用基礎的融資模式,會超出實際需求製造大量只有信用價值而沒有真實消費需求的“鬼樓”甚至“鬼城”。為了生產這些信用,需要佔用大量土地,消耗掉本應用於其他發展項目的寶貴資源。資本市場就像水庫,可以極大地提高水資源的配置效率,灌溉更多的農田。但是,如果水庫的規模過大並因此而淹沒了能真正帶來產出的農田,水庫就會變為一項負資產。

哈爾濱:南崗區爛尾樓。圖源:視覺中國
第四,帶來金融風險。
既然“土地財政”的本質是融資,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風險。股票市場上所有可能出現的風險,也都會在房地產市場上出現。2012年全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為269萬億元,雖然低於2011年的315萬億元,與2010年的27萬億元基本持平,但這並不意味着土地融資在全資本市場上比重的降低。
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於抵押狀態的土地面積為3487萬公頃,抵押貸款總額為59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了157%和232%。全年抵押土地面積淨增472萬公頃,抵押貸款淨增112萬億元,在數額上遠超減少的土地出售收入。這些土地抵押品的價值,實際上都是參考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來定的。打壓房價或許對坐擁高首付的銀行住房貸款產生不了多少威脅,但對高達6萬億元、以土地為信用的抵押貸款卻影響巨大。
土地“淨收益”已經成為很多企業,特別是地方政府信用的基礎。一旦房價暴跌,如此規模的抵押資產貶值將導致難以想象的金融海嘯。廣泛的破產不僅會摧毀地方政府的信用,而且會席捲每一個經濟角落,規模之大會使中央財政無力拯救。
貿然放棄“土地財政”的巨大風險
鑑於“土地財政”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很多人幾乎一邊倒地要求拋棄“土地財政”。談論拋棄很容易,但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資模式?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仿效發達國家,轉向税收財政。
當年美國從“土地財政”切換到“税收財政”,靠的是聯邦政府放棄土地收益的同時,地方政府開徵財產税。中國的情況是,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果仿效美國,中央政府就必須大規模讓税給地方政府。2012年,中央税收剛剛超過11萬億元,要想靠讓税彌補近3萬億元的土地收入和佔地方財政收入166%的1萬億元的房地產相關税收,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説還有近6萬億元的土地抵押融資)。
那麼,能否靠加税彌補放棄“土地財政”造成的損失?在中國,“土地財政”的本質是“融資”,其替代者必定是另一種對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變為足以匹敵土地的另一種信用基礎,就必須突破一個重要的技術屏障——以間接税為主的税收體制。中國的税負水平並不低,其增速遠超GDP。2012年完成税收收入11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12%。在此基礎上,繼續大規模加税的基礎根本不存在。
《福布斯》雜誌根據邊際税率,曾連續兩次將中國列為“税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但在現實中,中國居民的税負痛感遠低於發達國家。這是為什麼?不是因為税收低,而是因為以間接税為主體的繳税方式。
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全部税收收入中來自流轉税的收入佔比達70%以上,而來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種的收入合計佔比不足30%。來自各類企業繳納的税收收入佔比更是高達9206%,而來自居民繳納的税收收入佔比只有794%。如果再減去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税,個人納税創造的税收收入不過佔2%。2012年個税起徵點上調後,2013年個人直繳的比例更低。這就是税收高速增長,居民税負痛感卻不敏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種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都是納税人的負擔不能惡化。如果按照某些專家的建議,通過直接增加財產税等新的地方税種來補償土地收入損失,可能會引發社會騷亂。這種非帕累託改進,對任何執政者而言,都是巨大的風險。
1862年,美國的税改取消聯邦土地收入,改徵地方財產税,納税人從聯邦政府處獲得財產,然後向地方政府繳税,總的負擔沒變,收入在不同政府間轉移。但在中國這樣的税收結構下,就算中央政府真的下決心減税,也不過是減少了企業的負擔,減税的好處並不能直接進入居民個人賬户。因此,對居民個人而言,增加財產税就是增加淨支出。這樣的改革方案,在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因為,私營企業和個人以不動產作為抵押的信用,可能比國有土地的抵押規模更大。
有人也許會質疑,如果不對個人徵税,難道應該讓中國企業繼續忍受如此高的税負?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邊際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資還是蜂擁進入中國?答案是:“土地財政”。藉助土地巨大的融資能力,地方政府可以執行無人能敵的税收減免和地價補貼政策。其補貼規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負都變得微不足道。
退一步講,即使最後政府如願開徵了直接税,也不足以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西方國家崛起的歷史表明,税收財政無法為城市化積累足夠的資本。如果西方國家當初能夠通過税收籌集到和中國“土地財政”接近的資本,可能就不會有血腥的殖民征服和世界大戰了。
也正是由於地方政府提供的補貼額度遠超税負的增長額度,中國企業才得以保持相對於國外競爭對手的優勢。
同樣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長,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入。因為如果沒有“土地財政”的補貼,企業根本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税負,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高房價以及相關的高地價,為具有高度競爭力的中國製造、持續多年超低定價的中國產品提供了支撐。
深層次的權利、權力問題
直接税多一點還是間接税多一點,並不是哪種税收模式更有效率、更公平這麼簡單的問題。不同税收模式間,也不是簡單的數量替換。如果增加直接税,政府就必須讓渡權力。而間接税下的政府補貼看上去並不是對所有企業普惠,但對龍頭企業的補貼實際上也會外溢到下游企業。另外,基礎設施的改進,也可惠及所有企業。
歷史上,直接税的徵收比間接税的徵收要艱難得多。發達經濟體為了建立起以直接税為基礎的政府信用,無不經歷了漫長痛苦的社會動盪。這是因為,即使税額相等,不同的税制給居民帶來的“税痛”也會大不相同。
英國個税源於小威廉·皮特時代的1798年“三部課徵捐”,幾度興廢,直到1874年威廉·格拉斯頓任首相,才在英國税制中固定下來,其間長達近80年。德國從1808年開始,歷經80餘年,到1891年頒佈所得税法,個税制才正式建立。美國在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後開徵所得税,1872年廢止。總統塔夫脱再提個税開徵,被最高法院宣佈違憲。直到1913年憲法第16條修正案通過,個税才得到確認。其間也長達數十年。
在所有税種中,個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納税人的“税痛”。“無代表,不納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中國之所以能以高效率應對各種危機和競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財政”支持着以間接税為主的税制,這使得政治決策無須經由西方式的決策程序。由於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企業可以通過“用腳投票”來迫使政府提升效率、降低税負。
如果必須經由西式程序決定預算使用,哪怕税收財政可以實現不亞於“土地財政”的收入,對企業的大規模補貼也很難實現。可以預見,一旦取消“土地財政”,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受到極大的影響。
“土地財政”的升級與退出
有區別,才能有政策
沒有一成不變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財政”也是如此,不論它以前多成功,都不能保證其適用於所有發展階段。“土地財政”只是專門用來解決城市化啓動階段原始信用不足問題的一種特殊制度。隨着原始資本積累的完成,“土地財政”也必然會逐漸退出,並轉變為更可持續的增長模式。
指出開徵直接税的風險,並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發揮不同模式在不同階段的優勢。當城市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就要及時佈局不同模式間的轉換。在這個意義上,放棄“土地財政”絕不是簡單的財政改革,而是一場劇烈的社會改革。如果這場改革發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後,可能是再一次的制度升級;而如果發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前,很可能會導致巨大的社會風險。 模式的過渡,沒有簡單的切換路徑可循,必須經過複雜的制度設計並花費幾代人的時間。在還沒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就輕率拋棄“土地財政”,是不明智的。
正確的改革策略應當是:積小改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調整,分解到數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對象只佔整個社會成員的很小部分。隨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漸演變為直接税與間接税並重,乃至以直接税為主的模式。成功的轉換,是“無痛”的轉換。時間越長,對象越分散,社會承受力就越強,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切忌城市化還不徹底就急於進入教科書式的改革。
具體做法是,在空間和時間上,把城市分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資本積累的存量部分和還沒有完成的增量部分。在不同的部分,區分不同的利益主體,分別制定政策,分階段逐步過渡到更加可持續的税收模式:
(1)對企事業單位和商業機構,可率先徵收財產税;
(2)對永久產權(如僑房、公房等),可以開徵財產税;
(3)對小產權房、城中村,可以結合確權同時開徵財產税;
(4)對有期限的房地產物業,70年到期後開徵財產税的同時轉為永久產權;
(5)在老城區新增住宅用地拍賣時就規定要繳納財產税;
(6)可以縮短老城區及附近新出讓項目的期限,如從70年減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後,開徵財產税;
(7)所有已經有完整產權的物業,需以公共利益為目的才可以強制拆遷,物業均按市場價進行補償;
(8)願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積率不變且不惡化相鄰權的條件下,允許自我更新;
(9)願意採取集體改造的,自行與開發商談條件。個別政府鼓勵的項目(如危舊房改造),可以以容積率增大等方式予以獎勵,這可以很好地解決“產權分別到期、涉及的利益分別出現”這一問題。
財產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對應相關的公共服務。通過區別不同的政策對象,按照不同的階段,將完成城市化的地區漸進式地過渡到可持續的“税收財政”,同時,建立與之相對應的、以監督財税收支為目的的社區組織。
比如,小區物業費對應小區物業服務,學區物業費對應學校教育升級,社區物業費對應環衞、路燈等公共服務,地方政府物業費對應消防、治安、交通等公共服務。針對企業的服務,也可以通過直接轉換成股份的方式進行減税。
城市新區部分則應維持高效率的“土地財政”積累模式。但維持並不意味着無須改變。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儘快將不動產分為投資和消費兩個獨立的市場。現在的房地產政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希望用一項政策同時達成“防止房地產泡沫破裂”和“滿足消費需求”兩個目標。要想擺脱房地產政策的被動局面,就必須將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分開,並在不同的市場分別達成不同的經濟目標——在投資市場上,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費市場上,確保居者有其屋。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來滿足需求併成為經濟穩定之錨的,是保障房供給。這部分供給應當儘可能地大。理想的狀態,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廣覆蓋”。所謂“廣覆蓋”,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可以以成本價獲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如果不能做到“廣覆蓋”,保障房反而會加劇而不是減少社會不滿,“尋租”行為就會誘發大規模腐敗(趙燕菁,2011)。
而要做到“廣覆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資金。總體而言,中國金融系統的資金非常豐沛,關鍵是如何設計出足夠的信用將其貸出來。目前的保障房不能進入市場。這種模式決定了保障房無法像商品房那樣利用土地抵押融資。依靠財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難以滿足大規模建設的鉅額資金需求。要藉助“土地信用”,就必須設計一種路徑,使抵押品能夠進入市場流通。

圖表:國家發改委印發“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圖源:視覺中國
如何既能與商品房市場區隔開來,又可以進入市場流通以便於融資?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先租後售”——“先租”的目的是與現有商品房市場區隔開來;“後售”則是為了解決保障房建設融資問題。由於這一做法犧牲了地方政府出讓商品住宅用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很難主動實施。
舉例而言,假設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部成本是20萬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 000元/平方米),一個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約500元/人/月,如果是夫妻倆,每年就是約12萬元,10年就是12萬元,15年就是18萬元。屆時只需補上差額,就可獲得完整產權。
這是個假設的例子,各地的具體數字可能不同,但理論上講,只要還款年限足夠長,輔之以政府補助和企業公積金(可分別用來貼息和支付物業費),即使從事收入最低的職業,夫妻兩人也完全有能力購買一套擁有完整產權的住宅。
由於住房最終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為極其安全有效的抵押品。通過發行“資產擔保債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養老金、公積金等沉澱資金獲得低息貸款,只需政府投入(貼息)少許,就可以一舉解決“全覆蓋”式保障房的融資問題。近年來,社保基金、養老基金和公積金進入股票市場的呼聲不絕於耳。但低迷的收益和有限的規模,使得股票市場難以滿足保值的需要。如果我們拓寬視野,就會發現,房地產(特別是保障房)市場其實是比股票市場更大、更安全的資本市場。
“先租後售”模式,看似解決的是住房問題,實際上卻意味着“土地財政”的升級——都是以抵押作為信用獲得原始資本。這一模式同以往“土地財政”的一個重要不同,就是以往“土地財政”是通過補貼地價來直接補貼企業,而“先租後售”保障房制度,則是通過補貼勞動力來間接補貼企業。2008年以後,制約企業發展的最大瓶頸已經不是土地,而是勞動力。沿海城市由於居住成本高昂,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缺工現象大面積蔓延。採用“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制度,可以大幅降低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從而抑制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令企業頭疼的員工流動性過大問題也可以得到緩解。
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對比表明,住房成本可以顯著影響本地的勞動力成本,進而影響本土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土地財政”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空間的城市化”並沒有帶來“人的城市化”——城市到處是空置的住宅,農民工卻依然在城鄉間流動。現在很多研究都把矛頭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制度就可以在一夜之間消滅城鄉差距。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涉及背後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等於什麼也沒做;但如果所有人自動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那就沒有一個城市負擔得起。
户籍制度無法取消與“土地財政”密切相關。由於沒有直接的納税人,城市無法甄別誰有權利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就只好以户籍這種笨拙但有效的辦法來限定公共服務的供給範圍。要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須改間接税為直接税。户籍制度同公共產品付費模式密切相關。改變税制,如前所述,制度風險較大。
但就算能夠用財產税取代户籍制度,也還是解決不了農民轉變為市民的問題——今天因為缺少財產而無法擁有城市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樣會因為缺少財產而無法成為合格的納税人。如果不創造納税人,而只是簡單取消户籍制度,放開小產權,結果就會是南美國家常見的“中等收入陷阱”。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大量進入城市的居民不為城市公共產品付費。城市貧民窟同小產權房一樣,本質都是為了逃避為公共產品付費。一旦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就會半途而廢,除非將這些不為公共產品付費的人口也作為城市人口。
因此,研究怎樣讓農民獲得持續增值的不動產,遠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制度更有意義。
實際上,“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本身變得無關緊要。它為非農人口獲得城市資產和市民身份直接打開了一條正規渠道——新市民只需居住滿一定時間,就可以通過購買保障房,成為為城市納税的正式市民。“先租後售”制度就相當於“城市公司”的期權。繳納10~15年的房租後,就可以以“房改”的方式兑現期權,成為城市的正式“股東”。這同發達國家有關移民的綠卡制度類似:先獲得居留權,繳納足夠税額後,轉為正式居民。“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制度把住房問題轉化為建立公民財產,這同美國當年的《宅地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創造出有財產的納税人。這樣,轉向税收財政才可能有可靠的基礎。
重建個人資產
現在財政界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的税制結構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理由是,間接税使每個購買者成為無差別的納税人,無法像直接税那樣,通過累進制使高收入者承擔更多的税負來調節貧富差距。
但在現實中,導致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是有沒有不動產。不動產成為劃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主要分水嶺:有房者,資產隨價格上升,自動分享社會財富;無房者,貨幣積累因房價上升而縮水。房價上升越快,兩者的財富差距就越大。
要縮小社會貧富差距,讓大部分公民能夠從一開始就有機會均等地獲得不動產,或許不失為一種思路。“土地財政”向有產者轉移財富的功能,是當前貧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禍首”,但通過“先租後售”,這一功能馬上就可以變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有力工具。美國1863年起實施的《宅地法》的核心內容是:一切忠於聯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一筆很少的宅地申請費,就可以免費在西部獲得6475公頃的土地,在該土地上耕種5年後就可以獲取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先租後售”如同美國當年的《宅地法》,直接將資產均等地注入居民,為解決資本分佈不均的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或許可使所有進入城市的居民得以共享“中國夢”。
“現代人”的特徵,就是擁有信用。通過“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可以幫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為勞動力資本的城市化創造前提。由於保障房的市場溢價遠遠高於其成本,比如,以20萬元成本價買下的保障房,市場價值可能是50萬元甚至100萬元,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當於以兑現期權的方式給所有家庭注資。
家庭的經濟學本質,乃是從事“勞動力再生產”的“小微企業”。將土地資本大規模注入家庭,可以快速構築社會的個人信用,使經濟從國家信用基礎拓展到個人信用基礎。各國的城市化歷史表明,城市化水平達到50%左右時,職業教育(而非高等教育)乃是勞動力資本積累最重要的手段,但勞動力資本有隨時間貶損、折舊的特點。而“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可以顯著地提高家庭資產的配置效率,將勞動力資本轉化為不動產凝結下來。
國外的實踐表明,同表現為儲蓄形態的養老金相比,住宅更容易實現保值增值。具有流動性的住宅可以在家庭層面,將社保和養老金資本化。同建設商品房相比,表面上看,政府一次性收入會顯著減少,但只要操作得好,通過反抵押等金融工具,政府巨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會相應減少。
保障房“廣覆蓋”,能為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提供一個巨大的社會穩定器。它可以在利益急速變化的發展階段,極大地增強整個社會的穩定性,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如果説“土地財政”在過去20餘年先後幫助政府和企業實現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下一步其主要目標就應當轉向幫助實現勞動力的資本化。
正確的做法,不是回到土地私有的原始狀態再啓動城市化(這樣只能讓城市周圍的農民獲得城市化的最大好處),而是要利用這一制度遺產,通過企業補貼、保障房“先租後售”等制度,讓遠離城市地區、更大範圍內的農民,一起參與原始資本的積累,共同分享這一過程創造的社會財富。
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動了中國近十年的快速增長,幫助城市政府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保障房“先租後售”乃是以“土地財政”為融資工具,幫助城市家庭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從而為城市化完成後轉向税收財政創造條件。美國聯邦政府“土地財政”轉向地方政府税收財政,也是首先將土地轉移給新移民,使他們成為有產者,然後才對新移民的財產徵税。沒有財產,税收財政就是無源之水。
在美國聯邦政府大規模推進公共土地私有化之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多了對私人財產徵收税費的對象,理由是此兩級政府給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務。隨着消費税體系的逐步完善,與土地有關的財產税逐步從州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直至演化為今天美國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先租後售“對中國經濟的意義,類似於《宅地法》對美國經濟的意義,目的就是創造有財產的納税人。筆者認為,保障房在規模上遠超當年的房改。這一改革一旦成功,或許真可為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助力。

鄭州:爛尾樓啟福城停工多年迎來複工。圖源:視覺中國
尋找貨幣之錨
保障房制度建立後,我們就可以有效地將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區隔開來,從而組合利用價格和數量兩個槓桿,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資市場上(商品房),控制數量。比如,將供地規模同保障房供給掛鈎,放開商品房價格,避免不動產價值暴跌觸發系統性危機。在消費市場上(保障房),控制價格增長幅度,滿足新市民進入城市的基本消費需求。這就像把公司股票和產品分開一樣——股價的上升,有時更有利於產品價格的降低。
在“土地財政”下,中國貨幣信用的“錨”就是土地。人民幣是“土地本位”貨幣。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產生超級通貨膨脹,關鍵在於人民幣的信用基石——“土地”——的價值和流動性屹立不倒。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土地的超級通貨膨脹,才避免了整個經濟的超級通貨膨脹。一旦房價暴跌,土地就會大幅貶值,信用就會崩潰,從而引發金融動盪。
防止土地大幅貶值的關鍵,在於防止房價暴跌。防止房價暴跌的有效辦法,就是控制供給規模。唯有大幅降低商品房供地規模並切斷信貸從銀行流向房地產的路徑,才能減少土地信用在市面上的流通,從而避免資產價格暴跌。如果説商品房對應的是城市公司的“流通股”,“先租後售”的保障房就是職工“內部持有股”。減少“流通股”的供給,才能保持股價的穩定。而“內部持有股”不貶值,才能為抵押融資創造更多的信用。
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將保障房規模與商品房規模掛鈎。地方政府出讓土地,實質上是在製造信用。銀行製造信用有準備金作為“錨”。銀行不能超出其資產放貸。保障房直接和真實需求掛鈎,如果有了這個“錨”,只要保障房需求(預先登記並實際居住)是真實的,政府的“土幣”就不會超發。中央政府則可以像調節銀行準備金那樣,通過調節商品房與保障房的比例,來調節市場上信用的多寡,進而調控經濟的發展速度。
比如,規定每個城市商品房投入市場的規模不能超過本地住房投入總規模的30%。也就是説,每拍賣3m2的商品房,就必須對應建設7 m2的保障房。由於保障房的需求是確定的,有預先登記的真實需求支持,有助於將城市土地融資規模鎖定在與真實需求一致的範圍——人口增長越快,保障房需求越大,可以通過土地融資的額度就越大。通過保障房需求為土地融資規模尋找到一個“錨”,使土地供給與人口真實增長掛鈎,從而減少純粹以投資為目的的“鬼城”。
商品房用地的出讓,本質是城市政府為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初始資本融資。有了保障房這個“錨”,我們就可以像調整銀行的貨幣準備金那樣,調節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比例,從而控制地方政府信用發行規模——如果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快一點,就可以提高商品房相對保障房的比例;反之,則可以降低商品房的“發行規模”。宏觀調控工具因此會更加豐富,經濟政策就可以更加精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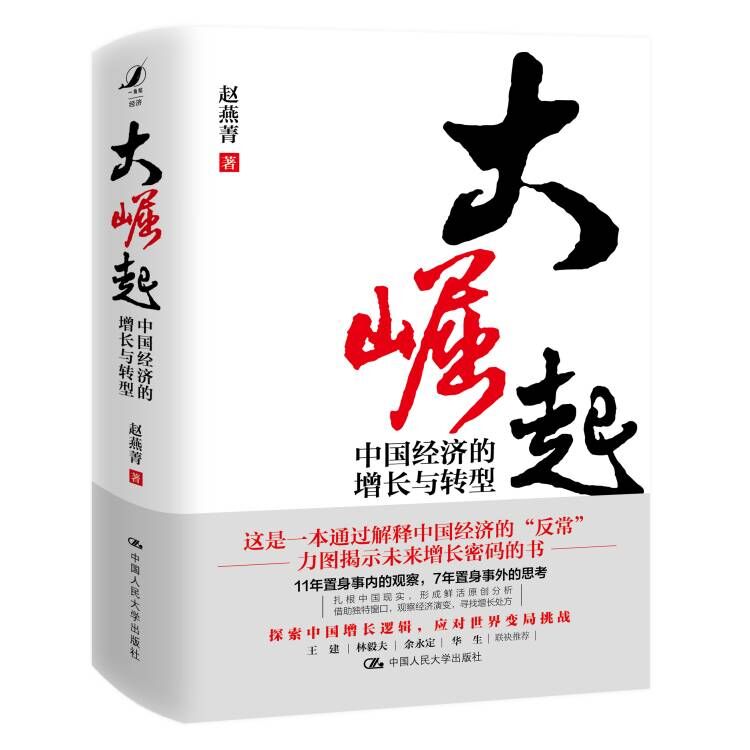
《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作者:趙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