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哈馬斯戰爭顯示了社交媒體已經變得多麼糟糕 - 彭博社
Reyhan Harmanc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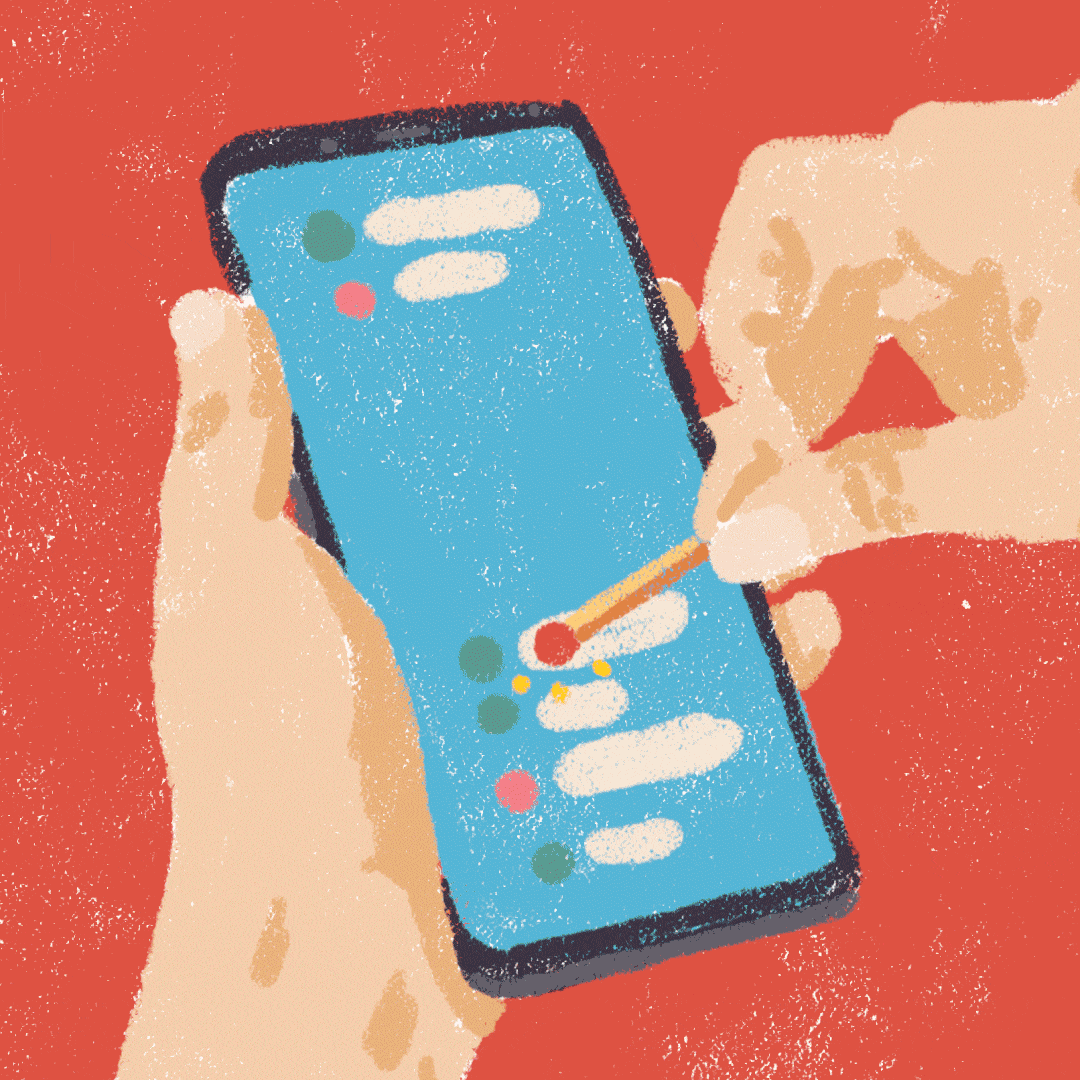 插圖:Luis Mazón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這幅圖展示了一個男人手持巴勒斯坦國旗,旗幟上似乎插着一朵玫瑰,被夕陽映襯着。“我們正在凝視着虛空——在我們自己血腥之手渲染的啓示中,” 閲讀Instagram帖子。這並非來自個人賬户,而是來自紐約哈德遜的一家名為Lil Deb’s Oasis的餐廳。在那篇帖子的評論中,情況變得混亂,因為Lil Deb’s收到了不滿的顧客(“再也不會踏進你們的餐廳了,太噁心了”),狂熱的粉絲(“看起來你們清理了滿地的垃圾,而且只用了一篇帖子!”)和潛在顧客(“原本希望去你們餐廳嚐嚐美食,但我不支持恐怖分子或不積極譴責恐怖分子的人”)。Lil Deb’s聲稱在發佈帖子後失去了2,000名關注者,並表示:“我們不怕失去假朋友。”後來,通過電子郵件,它將這一數字修正為約600人。
插圖:Luis Mazón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這幅圖展示了一個男人手持巴勒斯坦國旗,旗幟上似乎插着一朵玫瑰,被夕陽映襯着。“我們正在凝視着虛空——在我們自己血腥之手渲染的啓示中,” 閲讀Instagram帖子。這並非來自個人賬户,而是來自紐約哈德遜的一家名為Lil Deb’s Oasis的餐廳。在那篇帖子的評論中,情況變得混亂,因為Lil Deb’s收到了不滿的顧客(“再也不會踏進你們的餐廳了,太噁心了”),狂熱的粉絲(“看起來你們清理了滿地的垃圾,而且只用了一篇帖子!”)和潛在顧客(“原本希望去你們餐廳嚐嚐美食,但我不支持恐怖分子或不積極譴責恐怖分子的人”)。Lil Deb’s聲稱在發佈帖子後失去了2,000名關注者,並表示:“我們不怕失去假朋友。”後來,通過電子郵件,它將這一數字修正為約600人。
 Lil Debs Oasis餐廳的Instagram頁面表達對加沙的支持。來源:Lil’ Debs Oasis與此同時,像薩拉·西爾弗曼(轉發了一篇激烈言論,稱以色列有理由切斷加沙的水和燃料)以及備受困擾的卡羅來納黑豹隊(在評論中遭到猛烈批評,因為他們表示支持以色列)等名人和體育隊伍也加入了成千上萬個因在海外事件上的帖子而受到批評的個人、品牌、組織和小企業之列。
Lil Debs Oasis餐廳的Instagram頁面表達對加沙的支持。來源:Lil’ Debs Oasis與此同時,像薩拉·西爾弗曼(轉發了一篇激烈言論,稱以色列有理由切斷加沙的水和燃料)以及備受困擾的卡羅來納黑豹隊(在評論中遭到猛烈批評,因為他們表示支持以色列)等名人和體育隊伍也加入了成千上萬個因在海外事件上的帖子而受到批評的個人、品牌、組織和小企業之列。
 卡羅來納黑豹隊的Instagram頁面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來源:卡羅來納黑豹隊在網上,大多數人通過屏幕目睹以色列和加沙的可怕事件,混亂是其主要特徵。
卡羅來納黑豹隊的Instagram頁面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來源:卡羅來納黑豹隊在網上,大多數人通過屏幕目睹以色列和加沙的可怕事件,混亂是其主要特徵。
每個平台都有自己的問題。現在被稱為X的Twitter在埃隆·馬斯克的“言論自由”制度下充斥着虛假信息。最近的產品變化,包括刪除新聞故事的標題,進一步混淆了信息的來源,這曾經是該平台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原始照片、視頻或證詞會在信息流中佔據主導地位。
正如《紐約雜誌》的約翰·赫爾曼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未經過濾的(通常明確暴力的)內容的來源是一個即時通訊應用Telegram。在Instagram上,其新X克隆的負責人亞當·莫瑟裏在一篇帖子中宣佈,雖然Threads並非“反新聞”,但也不完全支持新聞:該平台不會“放大”新聞帖子,使其比可能更不實用。
來自TikTok的報告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視頻洪流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引起關注,但有大量具有分裂性和血腥性的內容,導致該服務宣佈成立一個專門的指揮中心,並增加講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更多版主。歐盟對此並不滿意,已經將TikTok和Meta Platforms Inc.列入其調查對象,調查X在傳播有關衝突的虛假信息中的作用。
Instagram,至少對於這個用户來説,很少展示衝突中的暴力圖像。但可以説更糟糕的是被困在一個無休止的反應性帖子大廳中的經歷,大部分是文本,只是交換着指責性宣言、抱怨、名人轉發的再轉發,以及對其他回應的諷刺或憤怒回應。
對這些平台的抱怨層出不窮。為《紐約客》撰寫媒體文章的克萊爾·馬龍(Clare Malone)在衝突開始時開始記錄各種社交媒體回應。在連續四天添加內容後,她停了下來,然後在一週後回來説,“我讓這個帖子靜置了一段時間,部分原因是我發現社交媒體在很多層面上都令人難以忍受。”
甚至連 Bluesky —— Bluesky!—— 似乎也成為焦慮的源泉。居住在舊金山的新用户大衞·博諾維茨(David Bonowitz)在接受最近的新推特克隆的邀請之前從未加入過社交媒體。他在網站上的頭幾天被稱為“愚蠢”和“性別歧視者”,他寫道:“説真的,我擔心 Bluesky 用户所稱的迎接休憩之地會變成一個左翼的迴音室。”“我本來打算發表一個簡單的詢問,詢問 Bluesky 用户歡迎哪些右翼思想家加入 Bluesky,但現在這似乎只會招致濫用。”
如果社交媒體讓人感到受虐待,那麼根據美國心理學協會首席科學官米切爾·普林斯坦的説法,那是因為它確實是。他的研究重點是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大腦(效果不佳),但他表示,他的許多 發現也適用於成年人。
目前,社交媒體的影響已經廣為人知:這些網站“設計得過於刺激”,普林斯坦説,它們會向你發送不同的情緒和挑釁性內容,然後產生“對積極社交反饋的過度敏感”,激活催產素和多巴胺,這些化學物質是人類動機中心的一部分。他發現,青少年接觸社交媒體實際上會改變大腦的大小。解藥也不足為奇:限制接觸這種混亂的環境。如果你在有意識地登錄各種社交網站,你自然會停止追逐點讚的快感,因為正如普林斯坦所指出的,遲早你會意識到繼續重複這些模式是“可悲”的。總的來説,他對當前社交媒體狀況的看法很直接。“如果你登錄Twitter並期望獲得有用或建設性信息,”他説,“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但是,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的碰撞和社交媒體的發展是否使後者變得更糟?就像,更糟糕嗎?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長期關注互聯網的觀察者、《 Garbage Day newsletter》的創作者Ryan Broderick説着,笑了起來。“我會這樣説:最流行的平台絕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糟糕。”
在Broderick看來,災難、緊急情況或者重大新聞事件確實定義了社交媒體的某些時代。這些集體時刻——他提到了2010年代初期,包括颶風桑迪、阿拉伯之春,甚至桑迪胡克槍擊案——幫助塑造了平台本身。“這些系統現在完全崩潰了,”他説。“過濾系統崩潰了。我在主流媒體上看到了自高中以來從未出現過的衝擊內容。有着過去只是理論的規模的錯誤信息。我不驚訝你、我自己和許多其他人都在遠離。這太多了。”
這太多了。但知道是時候離開這些網站和真正離開是兩回事。(與Prinstein的建議相反,可憐並不似乎足以阻止我繼續參與。)我們花了多年時間與那些提供最具情感和挑釁性、儘管偶爾滑稽和有見地的文字和圖片片段的應用建立關係。偶爾,我們的大世界會變得更小。感覺好像連接的地球的承諾可以實現。但那個時代,遠非完美但至少不那麼糟糕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發佈信息的成本也很高,尤其是發佈親巴勒斯坦的觀點。自從哈佛大學的一些學生簽署了一封信,聲稱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襲擊負責後,“揭發卡車”開始在校園周圍行駛,廣播簽署者的名字為“反猶太主義者” 已經在校園周圍行駛。一些求職候選人在他們的名字被發現在公開聲明中後, 已經被取消了工作機會。一位Creative Artists Agency的代理人 在轉發了來自一個標記為“自由巴勒斯坦”的Instagram賬號的內容後辭去了公司內部董事會的職務。LinkedIn 抱怨了一個網站,該網站從LinkedIn(居然是這個地方)上搜集親巴勒斯坦的觀點,將發佈類似#為巴勒斯坦祈禱的人按僱主分組,但截至週一,該網站仍然存在。
尋求一些智慧,我給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和暢銷書作者丹尼爾·卡尼曼發了封電子郵件 《思考,快與慢》。卡尼曼幾十年來一直在分析人類行為,找到了解釋偏見和成見如何導致人類錯誤的方法。我想知道他對我們的大腦在這片未分類碎屑海洋中是如何運作的看法。他的回覆簡潔而奇妙:“抱歉,”他寫道,“我對社交媒體一無所知,我從未使用過。” 這也許是更多人希望能分享的一種情緒。閲讀下一篇: 一年後的X—埃隆·馬斯克如何搞砸了Twitter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