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Neuralink的第一位患者?Noland Arbaugh關於他的腦植入物 - 彭博社
Ashlee Vance
 Arbaugh,第一個接受Neuralink腦機接口植入的人類。
Arbaugh,第一個接受Neuralink腦機接口植入的人類。
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彭博商業週刊
 美國總統喬·拜登於週日退出了2024年總統競選,支持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成為民主黨提名人,距離大選不到四個月。
美國總統喬·拜登於週日退出了2024年總統競選,支持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成為民主黨提名人,距離大選不到四個月。
攝影師:塞繆爾·科倫/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Noland Arbaugh仍然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關於他的生活如何發生如此巨大而又非凡的轉變的許多關鍵細節。他如何成為Noland Arbaugh,一名名人賽博格。
那是2016年中期,他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塔魯卡的Island Lake Camp作為體育顧問休息的第一天。當時,Arbaugh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學生,之前兩個夏天都在這個兒童夏令營工作過。人們和周圍的環境,包括附近的人工湖,都很熟悉,這一天和以往的許多日子一樣。他計劃和一羣朋友一起去湖邊。
 Noland Arbaugh與繼父David Neely在家中。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彭博商業週刊當Arbaugh和他的同伴到達時,水裏已經有人了。在岸邊和朋友聊天后,Arbaugh和另外幾個男孩衝向水中加入其他人。他們的計劃是跑進去,把在湖中嬉戲的女孩們浸濕。“我們就像一起跳進海里一樣一起跳進去的,”Arbaugh説。“那兩個傢伙站起來,然後去把女孩們抱起來之類的。而我就再也沒浮上來。”
Noland Arbaugh與繼父David Neely在家中。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彭博商業週刊當Arbaugh和他的同伴到達時,水裏已經有人了。在岸邊和朋友聊天后,Arbaugh和另外幾個男孩衝向水中加入其他人。他們的計劃是跑進去,把在湖中嬉戲的女孩們浸濕。“我們就像一起跳進海里一樣一起跳進去的,”Arbaugh説。“那兩個傢伙站起來,然後去把女孩們抱起來之類的。而我就再也沒浮上來。”
阿爾鮑跳入水中時,不知何時有什麼東西或某人——他仍然不確定是什麼——猛擊了他頭部的左側,讓他昏迷了一會兒。當他恢復意識時,臉朝下浮在水中,他試圖移動但無法動彈。一種莫名的平靜降臨在他身上。阿爾鮑立刻意識到自己癱瘓了,而且他無能為力。他屏住呼吸思考着自己的困境。十秒。十五秒。二十秒。附近似乎沒有人,他再也堅持不住了。“我想,‘好吧,現在是個好時機,’”他説。“我基本上喝了一大口水就昏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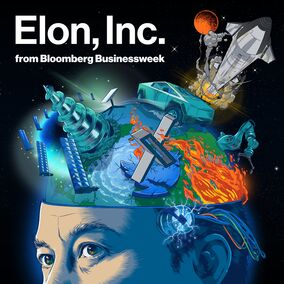 ## 埃隆公司
## 埃隆公司
神經鏈接首位患者講述
33:04
收聽並訂閲埃隆公司的 Apple, Spotify 和 彭博終端*。*
兩名同事發現了阿爾鮑並將他從湖中拉了出來。他在岸邊醒來,然後再次昏迷。下一次醒來時,他在一輛救護車裏,一名急救人員大聲猜測阿爾鮑的頸部以下癱瘓,並説他很快將被轉移到直升機上送往醫院。然後他再次昏迷。當他在醫院醒來時,阿爾鮑正在準備手術,以處理很快會被確認為脊椎脱位的問題。雖然昏昏沉沉但仍然不慌不忙,他在麻醉之前請求護士等手術結束後再打電話給他的母親米婭·尼利。他覺得醫生們最好在手術結束後有確切的消息,而不是在手術過程中讓他媽媽擔心。
在湖邊發生的事故徹底改變了這位22歲年輕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學會如何在他的電動輪椅上移動,通過吸氣和呼氣來控制一個管子,以不同的力量使機器朝不同方向移動。他還得弄清楚如何用嘴裏拿着的棍子戳iPad來使用電腦。他和他的家人花了很多時間處理醫院、保險公司和護理人員。
 這個植入物讓阿爾鮑能夠相對輕鬆地玩電腦遊戲。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彭博商業週刊今年一月,阿爾鮑成為了第一個接受埃隆·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開發的腦植入器的人,作為臨牀試驗的一部分。這個設備不會幫助阿爾鮑再次行動,但它確實承諾幫助他克服一些身體限制,讓他可以通過思考命令來控制他的筆記本電腦。他已經開始使用植入器在網絡上穿梭並與朋友交流,而不是在iPad上敲擊。
這個植入物讓阿爾鮑能夠相對輕鬆地玩電腦遊戲。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彭博商業週刊今年一月,阿爾鮑成為了第一個接受埃隆·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開發的腦植入器的人,作為臨牀試驗的一部分。這個設備不會幫助阿爾鮑再次行動,但它確實承諾幫助他克服一些身體限制,讓他可以通過思考命令來控制他的筆記本電腦。他已經開始使用植入器在網絡上穿梭並與朋友交流,而不是在iPad上敲擊。
雖然其他人也植入了類似的設備,但阿爾鮑成為了最為公開的接受者。部分原因是因為埃隆·馬斯克所做的一切都受到巨大關注。阿爾鮑在這裏首次分享了他的故事。顯然,他對癱瘓並不開心。但他説這是有原因的,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科學是上帝對他的計劃的一部分。
現年30歲的阿爾博(Arbaugh)與他的母親、繼父大衞·尼利(David Neely)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塔維塔(Tavita)一起住在亞利桑那州尤馬市。他們住在一條土路旁邊的一座簡樸的人造家園裏,周圍是沙漠和灌木叢。在後院,這個家庭養着雞、公雞、鵪鶉和火雞,還有一個大圍欄裏養着幾隻尼日利亞侏儒山羊。
 米婭·尼利(Mia Neely)和家裏的一些動物。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John Francis Peters)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小時候,阿爾博參加體育運動,加入學校樂隊和國際象棋隊。他有一羣親密的朋友,發現學校很容易——事實上,他經常逃課,只是為了參加考試,而他通常都能取得好成績。後來,他去了德克薩斯州的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攻讀政治科學和國際研究,同時參加了學校提供的軍事學員團體。幾年後,阿爾博開始更頻繁地逃課,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調酒和和朋友們一起玩耍。“我最終想要旅行,成為一個遊牧的吉普賽人,什麼也不做,”他説。
米婭·尼利(Mia Neely)和家裏的一些動物。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John Francis Peters)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小時候,阿爾博參加體育運動,加入學校樂隊和國際象棋隊。他有一羣親密的朋友,發現學校很容易——事實上,他經常逃課,只是為了參加考試,而他通常都能取得好成績。後來,他去了德克薩斯州的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攻讀政治科學和國際研究,同時參加了學校提供的軍事學員團體。幾年後,阿爾博開始更頻繁地逃課,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調酒和和朋友們一起玩耍。“我最終想要旅行,成為一個遊牧的吉普賽人,什麼也不做,”他説。
當然,由於事故,所有這些計劃都煙消雲散了。但是,阿爾博看起來是一個隨和、聰明的年輕人,他以一種淡定、耐心的方式談論自己的傷勢和病情,口音中帶着德克薩斯州的特有輕鬆愉快的腔調,這種腔調可能是他在德克薩斯州期間習得的。他留着小鬍子,兩個耳垂上戴着小耳環。偶爾,阿爾博的身體會抽搐,他會請求23歲的塔維塔幫忙,拉伸他的手臂或腿,因為它們被扭曲成一個棘手的姿勢,這對兄弟倆顯然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阿爾鮑在事故之後仍然有他的朋友和家人,但他花了幾年時間試圖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有時他感到無助,覺得自己是個負擔。儘管他申請了工作,但他無法用iPad快速地打字以滿足打字速度的標準。他説:“對我來説做很多事情很困難。我嘗試過其他事情,但我做不來。”他考慮完成大學學位,但無法從學校獲取成績單,因為有未償還的學生貸款。“我確信我會和父母呆在一起,只要他們能容忍我,然後,某個時候,我會被送進養老院,對此我無能為力,” 阿爾鮑説。
然後去年九月,他接到了他的軍校室友格雷格·貝恩的電話。貝恩讀到了《彭博社》的一篇報道,説Neuralink正在尋找第一個嘗試其腦植入裝置的患者。阿爾鮑從未聽説過Neuralink,所以貝恩向他解釋了基本概念。這種腦-計算機接口植入裝置有潛力讓癱瘓的人通過思維與計算機進行交互。“我當時就想,‘哦,聽起來挺酷的,’” 阿爾鮑説。
美國公眾對大腦芯片植入的看法
支持或反對每種用途的成年人比例
來源:2021年11月1日至7日進行的皮尤調查
貝恩幫助阿爾鮑填寫了關於他的傷勢性質、他仍然能做多少運動、是否吸煙或飲酒或吸毒、是否有其他醫療狀況等的在線問卷。阿爾鮑以前並不是一個重度飲酒者或吸煙者,但大約兩年前他完全戒掉了,這是他自我改進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還包括學習數學、科學和語言,以及聽一系列有聲讀物。“我只是決定要開始做些有意義的事情,這讓我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他説。
Neuralink第二天聯繫了阿爾鮑,很快開始進行電話面試。幾周後,公司要求他前往巴羅神經研究所在鳳凰城進行面對面測試,其中包括測量他的頭骨厚度和大腦與頭骨之間的間隙。作為醫療官僚和延誤的老手,阿爾鮑很高興看到整個翼被清空以保密他的到來,並且測試由一組專注於他的醫生和護士迅速進行。儘管最終決定尚未做出,但醫院的一些人開始向阿爾鮑透露他是首選候選人。
“這太棒了,因為你可以看到每個人有多興奮,”他説。“你可以感受到這種能量。很奇怪,因為他們一直告訴我見到我是多麼榮幸,以及我在做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這種感覺非常超現實。” 一月份,Neuralink通知阿爾鮑,他將成為第一個接受植入的人。
當你因頸部以下癱瘓時,你剩下的最後一點正常感來自你的大腦。阿爾鮑允許Neuralink直接、物理地訪問他的大腦,這個過程帶有所有嚴重手術的標準風險,以及對如此新事物的未知風險。醫生們將移除他的部分頭骨,並將Neuralink的硬幣大小設備與其帶有電極的線纜——一種從未在人類身上測試過的外來物體——插入他的大腦。
阿爾鮑得到了他的媽媽和繼父的祝福,如果出了什麼問題,他們仍然會是照顧他的人。他還花了幾個小時與貝恩和其他朋友辯論這個手術的好處。一個朋友警告他説,馬斯克“一貫以進步為重,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情”,阿爾鮑説。“他想讓事情發生,不在乎過程中發生了什麼。”另一個朋友提到了圍繞着Neuralink對動物進行植入測試的負面故事,並認為阿爾鮑可能會因為手術而遭受某種可怕的後果。
 Neuralink團隊的成員給了阿爾鮑這些簽名的他頭部的模型。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作為馬斯克的粉絲,阿爾鮑反駁了。他質疑了關於動物的故事的可信度。他還讀過一篇關於馬斯克在SpaceX首次將人類送入太空之前的行為的報道。馬斯克當時無法入睡,為宇航員的安全祈禱,儘管他並不是一個信仰虔誠的人。“那真的讓我放心了,”阿爾鮑説。“這讓我覺得他不會做這件事,如果他覺得會有不好的結果的話。”
Neuralink團隊的成員給了阿爾鮑這些簽名的他頭部的模型。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作為馬斯克的粉絲,阿爾鮑反駁了。他質疑了關於動物的故事的可信度。他還讀過一篇關於馬斯克在SpaceX首次將人類送入太空之前的行為的報道。馬斯克當時無法入睡,為宇航員的安全祈禱,儘管他並不是一個信仰虔誠的人。“那真的讓我放心了,”阿爾鮑説。“這讓我覺得他不會做這件事,如果他覺得會有不好的結果的話。”
阿爾鮑説,最重要的是,他的信仰推動着他前進。他確信上帝引導他戒煙和戒酒,因為這使他有資格參加試驗,他也確信上帝選中了Barrow神經研究所作為手術地點,因為離他家只有幾個小時,這使整個過程變得可行。“我一點都不擔心,”阿爾鮑説。“我看到了很多為我連接的點,這些點都符合這個情況。我的事故是如此的離奇,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上帝為我準備了什麼。當我開始做所有的Neuralink的事情時,我就想,‘好吧,這就是了。’”
Arbaugh於週日,1月28日,凌晨5點左右抵達醫院。Musk原計劃在手術前與他見面,但他的私人飛機出了問題。兩人只能通過短暫的FaceTime聊天,而Musk在手術進行時抵達了醫院。
手術持續不到兩個小時。當Arbaugh醒來時,他看到母親在他身邊。他們對視了幾秒鐘,Mia Neely問他是否沒事。“他説,‘你是誰?我不認識這個人,’”Neely回憶道。她哭了起來,試圖引起醫生的注意,但卻看到Arbaugh臉上露出了一絲笑意。他事先策劃了這個玩笑。“我想讓她知道一切都沒事,緩解緊張氣氛,”Arbaugh説。
 Arbaugh和他的狗Grace一起出鏡,他夢想成為一名作家。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大約20年來,研究人員一直在人體上進行類似於Neuralink的設備的實驗,但這些設備通常笨重,通常需要醫療團隊幫助操作。因此,這些植入物幾乎總是在醫院和實驗室環境中使用。在過去幾年裏,一些初創公司開發了更現代化的產品和植入方法。所有這些公司都希望使用這些植入物幫助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在非醫院環境中控制機器。
Arbaugh和他的狗Grace一起出鏡,他夢想成為一名作家。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大約20年來,研究人員一直在人體上進行類似於Neuralink的設備的實驗,但這些設備通常笨重,通常需要醫療團隊幫助操作。因此,這些植入物幾乎總是在醫院和實驗室環境中使用。在過去幾年裏,一些初創公司開發了更現代化的產品和植入方法。所有這些公司都希望使用這些植入物幫助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在非醫院環境中控制機器。
植入物通過收集大腦神經元發射時的數據來運作。藉助人工智能軟件,可以將特定的神經活動模式與某些動作相匹配,將這些數據轉化為行動,並在計算機上執行。例如,儘管Arbaugh無法移動手,但他可以想象移動手。Neuralink植入物可以識別這種情況,然後將意圖傳輸到附近的筆記本電腦或智能手機,使他能夠在屏幕上移動光標。這意味着Arbaugh可以玩遊戲、購物、選擇有聲讀物,並與在線世界進行互動,就像其他人一樣。
“你可以感受到這種能量。很奇怪,因為他們一直告訴我見到我是多麼榮幸,以及我正在做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這種感覺非常超現實。”
大多數腦植入物初創公司使用的技術是在神經元附近,但並非直接貼近神經元的位置放置電極。一個例子是Synchron公司的一種設備,可以通過相對安全的程序嵌入到大腦的血管中,而無需切開頭骨。Precision Neuroscience公司有一款產品位於大腦表面上。為了獲得更清晰的信號,Neuralink將電子線直接滑入腦組織,這種方法需要更具侵入性的手術。Arbaugh試驗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植入物植入程序的安全性,並且設備可以長時間留在某人的頭部而不會造成損傷。
除了更接近行動,Neuralink的設備比大多數競爭對手擁有更多的電極和更高的數據帶寬。有了更高的帶寬,植入物可以從大腦接收到更豐富的信號,使像Arbaugh這樣的人可以比使用其他產品更快更有效地操作他的電腦。如果這種技術運作良好,它對於不僅患有癱瘓,還患有像ALS和中風等疾病的人來説將是一個巨大的福音,因為他們的移動和交流能力已經受到損害。
在回家的頭幾周,Arbaugh在家裏的客廳和廚房裏接受了Neuralink團隊的測試。在研究環境中,腦植入物患者通常需要在兩到四個小時後休息,因為精神和身體會受到壓力,但Arbaugh可以連續工作長達10小時。該設備也勝過了它的前輩。從第一天開始,他就開始打破用於基準測試腦機接口植入物性能的典型測試的速度記錄。
世界為Arbaugh重新打開了大門。他可以相對輕鬆地玩遊戲,比如Sid Meier的文明和下棋。他可以在電腦上輕鬆地在網站和有聲讀物之間切換。而且他可以在牀上做所有這些事情,這比坐在輪椅上,試圖讓他的嘴棒與iPad對齊要舒適得多,也不會引起痙攣。
在早期,Arbaugh必須學會如何調整Neuralink的軟件以適應他的大腦模式,並領會將思維轉化為行動的要領。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過程變得如同第二天性。Arbaugh可以一邊與某人交談,一邊同時下棋。他似乎已經擁有了超能力。
 阿爾博準備上牀睡覺,與他的母親和繼父在一起。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但是大約一個月的練習後,他發現自己對屏幕上的光標控制不夠精確,並注意到他的思維與計算動作之間存在延遲。這些問題是由於阿爾博腦中的電極線纏繞的線程移動比Neuralink在動物試驗中看到的要多得多。這破壞了他的思維和計算機之間連接的質量。他的超能力開始消失。
阿爾博準備上牀睡覺,與他的母親和繼父在一起。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但是大約一個月的練習後,他發現自己對屏幕上的光標控制不夠精確,並注意到他的思維與計算動作之間存在延遲。這些問題是由於阿爾博腦中的電極線纏繞的線程移動比Neuralink在動物試驗中看到的要多得多。這破壞了他的思維和計算機之間連接的質量。他的超能力開始消失。
該公司尚未披露有關導致線程移動如此之多的詳細信息。一個問題可能是人類大腦比動物大腦更大,搖晃更多。阿爾博的頭骨也比平均厚,這可能影響了線程安置在他的組織中的方式。阿爾博將繼續使用當前版本的植入物,但很可能Neuralink將調整其手術程序,可能還包括植入物本身的部分,以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它朝着今年在更多患者身上測試該設備的方向前進。
“一旦你嘗試使用它,你就停不下來了”
技術產品幾乎總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進;阿爾博曾與貝恩討論過,他可能會收到可能是任何人收到的最糟糕的Neuralink植入物。但阿爾博之所以同意試驗,正是因為這類問題可能會發生。他希望通過幫助Neuralink消除植入物的任何缺陷來幫助其他人。儘管如此,他新發現的能力的喪失仍然讓人痛苦。
“我開始失去對光標的控制。我以為他們做了一些改變,這就是原因,”阿爾鮑説。“但後來他們告訴我,我的大腦中的線被拉出來了。起初,他們不知道這會有多嚴重或者有多少相關信息。
“聽到這個消息真的很難受。我以為我可能只能用它一個月,然後我的旅程就要結束了。我以為他們只會繼續收集一些數據,然後真的會轉向下一個人。我有點哭了。”
Neuralink開始努力看看能做些什麼來解決問題。其軟件工程師調整了從阿爾鮑的神經元記錄數據的算法,並對數據分析和傳輸方式進行了更改。阿爾鮑現在又開始創造記錄。“我打賭下一個得到這個的人會和我有一樣的感受,”他説。“一旦你嘗試使用它,你就停不下來。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
阿爾鮑每天使用他的植入物10到12個小時,只有在充電或睡覺時才休息。他每天早上都會在筆記本電腦上閲讀德克薩斯州Gateway教堂的在線靈脩,然後評估他的幻想棒球名單的狀態。他仍在學習、聽有聲書和玩很多視頻遊戲。
看到阿爾鮑的行動真是一種魔力。他過去常常用語音命令和嘴棍來完成他的日常任務。如果他在聽有聲書,他就不能使用語音轉文本功能進行交流,除非他停止有聲書,用嘴棍尋求幫助,然後跳到一個新的應用程序。現在他可以輕鬆地在不同應用程序之間切換。
尼利(Neely)是一位青年牧師,有時簡直無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她會在阿爾鮑(Arbaugh)的卧室裏與他一起觀看節目,而他卻在玩一款視頻遊戲——只用他的思維。然而,對她來説最大的勝利是,阿爾鮑更快樂,疼痛減輕了,因為他可以以最舒適的姿勢使用電腦。“我們看到了這一面,不再有痛苦,不再不斷地去調整他,也不再因為他感到沮喪而把嘴裏的咬嘴器射出來,”她説。“這太棒了。這是一種祝福。”
 阿爾鮑在與Neuralink團隊交流時進行着以Neuralink為重點的鍛鍊。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John Francis Peters)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阿爾鮑將他的植入物命名為Eve的部分原因是,他説,上帝將Eve呈現給亞當作他的幫手。最近,他開始用通過植入物控制的光標在電腦屏幕上追蹤字母。這是訓練Neuralink軟件識別阿爾鮑所思考的單詞的第一階段。阿爾鮑希望很快就能夠思考整個句子,並讓軟件知道他想説什麼。他長久以來一直夢想成為一名奇幻作家,並希望寫一部小説。
阿爾鮑在與Neuralink團隊交流時進行着以Neuralink為重點的鍛鍊。攝影師:約翰·弗朗西斯·彼得斯(John Francis Peters)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阿爾鮑將他的植入物命名為Eve的部分原因是,他説,上帝將Eve呈現給亞當作他的幫手。最近,他開始用通過植入物控制的光標在電腦屏幕上追蹤字母。這是訓練Neuralink軟件識別阿爾鮑所思考的單詞的第一階段。阿爾鮑希望很快就能夠思考整個句子,並讓軟件知道他想説什麼。他長久以來一直夢想成為一名奇幻作家,並希望寫一部小説。
除此之外,阿爾鮑並不完全確定如何利用他的聚光燈時間。他希望找到一種通過這種經歷謀生的方式,這樣他就不那麼依賴家人,他們也不必那麼經常照顧他。“我哥哥照顧我已經八年了,”阿爾鮑説。“他需要過自己的生活。”如果命運允許的話,他真的很想賺足夠的錢為他的媽媽建一所房子,以感謝她為他所做的一切。
Arbaugh已同意將設備留在他的頭部,並向Neuralink提供數據一年。之後,他和公司將討論他是否想要停用甚至移除設備。Arbaugh懷疑他會想要保留它,甚至在產品推出新版本時轉向下一個版本。“我想要升級,”他説。“希望他們會把我列入候選名單。”
閲讀更多: 關於馬斯克的Neuralink及其首個人類腦植入物的一切
喬·拜登(Joe Biden)以他的決定將總統選舉推向了未知領域,他決定退出競選,這在美國政治現代時代是前所未有的舉動。決定退出競選,這是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位不尋求連任的總統,他在週日退出了2024年總統競選,並支持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59歲,成為民主黨提名人,將在不到四個月後與唐納德·特朗普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