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圖加特到香港,“風道”為酷熱帶來緩解 - 彭博社
bloomberg
 清晨時分,霧氣如紗幔般飄蕩在斯圖加特城區上空。這座城市的特殊地形使其極易積聚空氣污染物。
清晨時分,霧氣如紗幔般飄蕩在斯圖加特城區上空。這座城市的特殊地形使其極易積聚空氣污染物。
攝影師:Christoph Schmidt/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 為對抗熱浪,全球城市正追隨風的軌跡(音頻)
## 為對抗熱浪,全球城市正追隨風的軌跡(音頻)
16:02
在斯圖加特炎熱的夏日搭乘電車,你可能會聽到人們抱怨schlechte Luft——即污濁空氣。“不是邪惡的那種糟糕,“柏林洪堡大學城市人類學研究員Indrawan Prabaharyaka解釋道,“而是粘膩的空氣——那種過於厚重的窒息感。”
這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沿內卡河而建,坐落於寬闊的盆地狀山谷中。居民們早已意識到,陡峭的山勢會困住尾氣與工業廢氣,形成經久不散的污染雲團。但特殊地形也孕育着天然解藥:緩慢流動的自然風穿梭城市,夜間將山坡草甸與葡萄園的清涼空氣引入谷底的市中心。當地人稱之為Luftbahnen(風道)、Kaltluftschneisen(冷空氣走廊),或最常用的Frischluftschneisen(新風走廊)。
如果你足夠幸運,可能會遇到一位斯圖加特本地人——普拉巴哈里亞卡説通常是年長者——他們能準確指出空氣在社區周圍的流動路徑。“居民們對當地微氣候非常瞭解,“這位雅加達出生的人類學家説道。在密集的斯圖加特西區,租户們常抱怨當地空氣凝滯,與綠樹成蔭的郊區"更稀薄"的大氣形成對比。
 內卡河沿岸葡萄園環繞的山坡不僅是風景畫:它們更是斯圖加特城市通風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攝影師: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圖片聯盟 via Getty Images在奔馳和保時捷總部所在地——這座穩重富裕的工業城市,當地人對風向瞭如指掌的特質顯得別具一格。但據普拉巴哈里亞卡研究,這種認知實則反映了該市長達八十年的獨特城市氣候學實驗。作為其“空氣走廊”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以及他正在進行的當前項目,自1950年代以來,斯圖加特始終以最大化自然氣流為導向規劃城市發展,禁止阻斷風道的建設,並保護能匯聚冷空氣的綠地。
內卡河沿岸葡萄園環繞的山坡不僅是風景畫:它們更是斯圖加特城市通風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攝影師: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圖片聯盟 via Getty Images在奔馳和保時捷總部所在地——這座穩重富裕的工業城市,當地人對風向瞭如指掌的特質顯得別具一格。但據普拉巴哈里亞卡研究,這種認知實則反映了該市長達八十年的獨特城市氣候學實驗。作為其“空氣走廊”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以及他正在進行的當前項目,自1950年代以來,斯圖加特始終以最大化自然氣流為導向規劃城市發展,禁止阻斷風道的建設,並保護能匯聚冷空氣的綠地。
隨着全球城市努力應對極端高温和空氣污染日益加劇的風險,這種圍繞風模式進行規劃的做法正吸引國際關注,尤其是在亞洲快速發展的特大城市。從香港門户造型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大樓,到新加坡濱海灣高樓羣刻意設計的通風廊道,這些城市天際線日益展現出對城市通風的新認知。
但説服政策制定者和房產投資者為城市"呼吸空間"買單仍面臨巨大障礙——在住房緊缺、擁有全球最昂貴房地產的一些城市尤其如此。
戰爭迷霧
利用自然風道淨化城市空氣的理念可追溯至20世紀初。作為德國汽車工業搖籃的斯圖加特曾飽受肺結核疫情和嚴重空氣污染困擾,特別是在戴姆勒-奔馳工廠沿內卡河擴張後。
但當該市在二戰前夕聘請首位城市氣候學家卡爾·施瓦爾布時,他的首要任務並非驅散有害霧霾,而是製造更多:為保護城市及工廠免遭空襲,施瓦爾布建立了一套屋頂"霧彈發射器"網絡,向大氣噴灑造霧化學品。
由於盟軍轟炸機採用新型雷達技術,人造霧障計劃最終失敗。但施瓦爾布注意到異常現象:人工霧障在城市某些區域迅速消散,卻在其他區域持續數日,意外繪製出一幅空氣流動圖譜。這座遭受重創的城市在戰後重建時,這場意外實驗教會了人們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通風。
施瓦爾布曾提議將斯圖加特市中心的建築高度限制在四到五層,這一模式延續至今,同時通過拓寬市區道路來擴展部分通風路徑。這些通風廊道與受保護的綠地相連,例如城市西緣的森林地帶,清涼的新鮮空氣得以由此流入。
隨着時間的推移,新建築的選址、高度、朝向和外立面都受到規劃法規的約束,以保護氣流通道。斯圖加特大學氣象學家于爾根·鮑米勒作為施瓦爾布的繼任者指出,城市最重要的風道——沿着內森巴赫溪流經市中心的路徑(儘管如今這條水道大部分已被混凝土覆蓋)——至今仍受到嚴格保護。
 從比爾肯科普夫山頂俯瞰,可見斯圖加特市中心低矮的建築佈局,這座人造山丘由二戰轟炸中損毀的建築廢墟堆積而成。攝影師:馬裏揚·穆拉特/圖片聯盟 via Getty Images鮑米勒解釋道,附近山丘上的草地和農田等開闊綠地夜間散熱迅速,成為"冷空氣生產區”。這些較冷空氣以每秒約2米的速度滲入城市,夏季能調節夜間温度,冬季則有助於驅散易滯留霧霾的逆温現象。“居民們告訴我,當太陽落山後坐在花園裏時,能明顯感覺到冷空氣正在湧入。“鮑米勒如是説。
從比爾肯科普夫山頂俯瞰,可見斯圖加特市中心低矮的建築佈局,這座人造山丘由二戰轟炸中損毀的建築廢墟堆積而成。攝影師:馬裏揚·穆拉特/圖片聯盟 via Getty Images鮑米勒解釋道,附近山丘上的草地和農田等開闊綠地夜間散熱迅速,成為"冷空氣生產區”。這些較冷空氣以每秒約2米的速度滲入城市,夏季能調節夜間温度,冬季則有助於驅散易滯留霧霾的逆温現象。“居民們告訴我,當太陽落山後坐在花園裏時,能明顯感覺到冷空氣正在湧入。“鮑米勒如是説。
自1992年起,斯圖加特將這些研究成果——包括氣流圖、污染濃度與城市温度數據——整合成氣候圖集用於指導規劃決策。相較於其他可能的建設方案,這套通風系統的實際效果難以直接量化。但該市現任氣候主管雷納·卡普在郵件中表示,空間模型顯示風道有效將冷空氣引入居民區,並減少了氣温不低於20℃(68℉)的"熱帶夜"天數。由於氣候變化,斯圖加特預計未來幾十年極端高温天數將翻倍。
鮑米勒指出,斯圖加特通風策略成功的最佳佐證是城市平均風速數據。在其他城市,密集的高層建築羣已被證實會使風速減半。“我們在市中心持續監測超過35年,“他説,“並未觀測到風速下降。”
亞洲實踐
過去20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最積極推行風道政策的國家。“我們知道已有40多箇中國城市採用這種方法並付諸實踐,“研究城市微氣候的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任超表示。根據自然資源部2019年頒佈的規劃要求,所有城市在制定或更新總體規劃時都必須完成風道規劃,北京、成都、澳門、濟南和武漢已相繼出台前瞻性方案。
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周圍籠罩着霧霾和空氣污染,這加劇了其關注,據估計在21世紀初每年導致40萬人過早死亡。中央政府在香港尋求解決方案,2003年SARS疫情曾在此造成約300人死亡。“那時,環境衞生確實是個熱門話題,“任説。
香港的"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同年成立,目標是打造"清潔衞生的香港”。在重建了"零號病人"呼吸道病毒在居民區的傳播路徑後,該小組建議新開發項目應優先考慮通風,促使建築師尋找使建築更具透氣性的方法。
任説,這就是為什麼2008年建成的香港政府總部設計得像一個敞開的門道。“如果你看它的形狀,會發現一個巨大的空洞。這都是因為通風評估。”
 香港中區政府合署內的大型開放空間反映了該市新的城市通風標準。攝影師:Paul Yeung/彭博社
香港中區政府合署內的大型開放空間反映了該市新的城市通風標準。攝影師:Paul Yeung/彭博社 香港西九文化區新建築羣拔地而起攝影師:Chan Long Hei/彭博社委員會的第二項建議——城市規劃者應研究如何增強街道周圍空氣流動——被證明更具挑戰性。香港歷來依靠天然海陸風降温,但這座擁有1500多座摩天大樓的現代都市,密集排列在香港島北岸與九龍對岸海岸線上。“我們築起了一堵磚牆,這就是為什麼行人高度的風力非常微弱,“任教授解釋道。
香港西九文化區新建築羣拔地而起攝影師:Chan Long Hei/彭博社委員會的第二項建議——城市規劃者應研究如何增強街道周圍空氣流動——被證明更具挑戰性。香港歷來依靠天然海陸風降温,但這座擁有1500多座摩天大樓的現代都市,密集排列在香港島北岸與九龍對岸海岸線上。“我們築起了一堵磚牆,這就是為什麼行人高度的風力非常微弱,“任教授解釋道。
借鑑斯圖加特經驗,香港在2006至2012年間繪製了自己的氣候地圖。但為全球建築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通風,與斯圖加特戰後重建情況截然不同。“我們無法直接套用德國方法,“任教授表示。香港轉而通過街道級科學評估對全城進行測繪,以保護現存風道,並尋找未來再開發中可能開闢的新風廊。
此後,任教授與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其他城市通風政策。長期受嚴重空氣污染困擾的北京,規劃者確定了五條沿盛行南北風向的主風道,這些風道被證實對空氣流動具有可測量影響。
降温趨勢
全球城市正日益認識到其佈局與天際線對熱島效應和空氣污染的累積影響。最新研究表明,雖然高層建築會阻擋風力,但其投射在周邊街道的遮陰區域能有效緩解熱島效應——這種效應源於混凝土、瀝青等吸熱材料導致建成區温度升高。街道設計同樣關鍵:倫敦中世紀風格的蜿蜒道路網絡,使得其升温幅度低於芝加哥這類採用規整網格佈局的城市,這得益於建築間熱輻射的獨特擴散方式。
迄今為止,多數城市通風項目都出於空氣質量考量。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新報告指出,這些措施同樣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方案,全球城市正在探索如何利用風道來緩解高温問題。
新加坡——這個氣温上升速度兩倍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城市,是首批嘗試利用風道調控温度的先行者。這座距離赤道僅85英里的土地稀缺島城開發強度極高,市中心温度可比郊區高出7攝氏度。
閲讀更多: 新加坡如何在城市升温中保持涼爽
新加坡國立大學城市氣候設計實驗室負責人袁超表示,在每年兩次的季風季節,沿海岸線南北向的較強風力可將氣温降至舒適水平。但季風間歇期,氣温會攀升至90華氏度(32攝氏度)以上,加上高濕度,沒有空調的生活令人難以忍受。“夜間空氣幾乎停滯,“他説,“我們看不到樹枝搖動(在樹叢中),因為近地面區域幾乎沒有氣流。”
 氣象站監測新加坡濱海灣的風速。該區域的新建項目旨在保持自然氣流。攝影師:Roslan Rahman/AFP via Getty Images
氣象站監測新加坡濱海灣的風速。該區域的新建項目旨在保持自然氣流。攝影師:Roslan Rahman/AFP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新加坡在建建築。多座新塔樓設有促進空氣流通的大型開放區域。攝影師:SeongJoon Cho/Bloomberg袁超指出,在季風間歇期,幾乎每個新加坡人都會整夜開着空調。“當人們使用空調時,機器本質上只是將熱量從室內轉移到室外,“他解釋道,“所有來自空調冷凝器的人為熱量都會滯留在街道峽谷中”,使室外氣温升高約2攝氏度。
2024年新加坡在建建築。多座新塔樓設有促進空氣流通的大型開放區域。攝影師:SeongJoon Cho/Bloomberg袁超指出,在季風間歇期,幾乎每個新加坡人都會整夜開着空調。“當人們使用空調時,機器本質上只是將熱量從室內轉移到室外,“他解釋道,“所有來自空調冷凝器的人為熱量都會滯留在街道峽谷中”,使室外氣温升高約2攝氏度。
為了探索如何最優規劃通風廊道,新加坡開發了能優化建模與模擬的工具。該國是首批構建”數字孿生城市“來預測開發項目對城市影響的先驅之一,而袁博士實驗室研發的微氣候數字平台,能模擬風力、人為熱源、熱島強度等物理因素。新加坡正通過這些模型完善城市風場數據採集方式。袁博士通過Zoom演示瞭如何運用多普勒激光雷達掃描技術追蹤氣流運動,優化城市風場模擬。“我們同時部署了近地面氣象站監測風速風向,這些高精度數據能驗證通風廊道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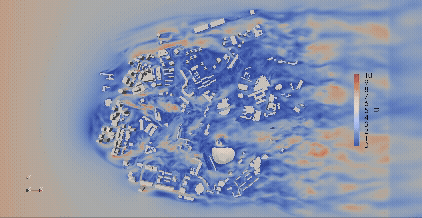 新加坡氣流激光雷達動畫顯示海風如何被中央商務區建築阻擋:“這裏形成了明顯的風牆效應”,研究員袁超解釋道。圖片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城市氣候設計實驗室這些工具已影響濱海灣新區的開發規劃。該區域波浪形摩天樓羣採用通透設計,塔樓間留有巨大間隙引入光線與氣流。“若完全封閉會怎樣?“袁博士反問道。
新加坡氣流激光雷達動畫顯示海風如何被中央商務區建築阻擋:“這裏形成了明顯的風牆效應”,研究員袁超解釋道。圖片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城市氣候設計實驗室這些工具已影響濱海灣新區的開發規劃。該區域波浪形摩天樓羣採用通透設計,塔樓間留有巨大間隙引入光線與氣流。“若完全封閉會怎樣?“袁博士反問道。
遁入虛空
儘管益處良多,但説服城市圍繞無形氣流進行規劃建設仍是少數成功的案例。畢竟,有多少土地所有者願意接受"世界上最昂貴地塊的最佳利用方式就是保持空曠"這樣的論點?
因此風道政策的先行者往往是中央規劃和土地管控嚴格的地區。“在新加坡就很簡單,我只需要説服負責規劃的城市重建局,“袁教授説,“他們信任我。”
在市民話語權更大的城市則困難得多。洪堡大學研究員瑪格麗塔·泰斯正在研究日本案例——該國在90年代末引入了城市氣候規劃。神户、東京和福岡效仿斯圖加特製作了氣候地圖集,但這些城市尚未啓動圍繞風道重構城市肌理的進程。“計劃制定了,但往往也被束之高閣,“她説。
日本案例反襯出斯圖加特經驗堪稱奇蹟。泰斯指出:“斯圖加特形成了市民、當局和決策者之間獨特的技術-政治-科學協同機制”,這才使風道建設成為可能。
這並非説該政策未引發波瀾。如今新建住房常引發衝突:斯圖加特房價高居德國前列,過去十年租金上漲60%,背後是長期滯緩的建房速度。土地所有者屢次起訴要求開發空地。在綠樹成蔭的羅爾路社區,居民雖允許普拉巴哈里亞卡考察他們的空氣通道,但某可能影響風道的開發項目仍引發訴訟大戰;最終開發商贏得了在未開發果園建造住宅的權利。
但認識到氣流的存在讓社區團體有了組織行動的依據,即便這是種無形之物。“斯圖加特對風道的保護是在’賦予某種虛空以地位’,“泰斯説道。
普拉巴哈里亞卡稱此為某種"泛靈論”——城市將那些可能被抹除的空隙視為景觀中的重要參與者。他興奮地看到這種觀念在西方城市出現:“我是印尼人,是東南亞人;我能從各類物體中看見靈魂,“他笑着説。
他指出歐洲城市居民通常回避這類觀念,但在斯圖加特,相似的思維已通過技術科學干預、政策與規劃等方式形成——只是剝離了精神層面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