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馬蒂奇:前南斯拉夫地區的危機,德國是最重要的推動黑手
guancha
編者按:二十六年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打着所謂“避免人道主義災難”旗號,繞過聯合國安理會,開始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大規模空襲。長達78天的轟炸造成2000多名無辜平民喪生,6000多人受傷,近100萬人流離失所。
二十六年後的 今天,北約與西方的陰影仍然籠罩在塞爾維亞的上空。自2024年11月以來,塞爾維亞已發生660多起抗議活動。這股由諾維薩德火車站頂棚坍塌事故引發的反武契奇示威浪潮,已成為自2000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下台以來,塞爾維亞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
前南聯盟信息部長的格蘭·馬蒂奇先生,曾親身經歷了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聯盟的全過程,在南聯盟同西方的信息戰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此,塞爾維亞在華留學生菲利蒲在他的BiliBili頻道上對話這位前南聯盟信息部長。觀察者網整理了文字內容,供各位讀者參考。 本文為下篇。
【上篇:這就是戰爭罪,根本不是他們所説的什麼干預、失誤、故障!】
**菲利蒲:**北約轟炸南斯拉夫26年後,再回頭看您會如何分析北約入侵南聯盟的理由?如果我們看中國方面的分析,經常會看到美國被認為是核心主導力量,但我記得我們曾經在討論中,或是您在寫文章時,經常提及德國的因素,這一點在中國輿論場上看到的不多,所以能否請您着重分析一下德國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格蘭·馬蒂奇:**討論北約入侵南聯盟時,其實這件事跟整個90年代和內戰是連在一起的,尤其是北約對波黑塞族共和國的轟炸,也就是1994年那段時期。現在很多分析人士——不管是西方的、東方的還是我們自己的,一直在研究北約轟炸南聯盟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因為任何靠轟炸達成的目的完全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彼時南聯盟對西方是持開放態度的,也願意跟西方對話,但南聯盟的這種姿態顯然沒法滿足西方的胃口。
所以分析這個問題有幾個不同的視角,當時是17個北約國家參加了對南聯盟的入侵,甚至參與轟炸的人裏面還有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當時他是葡萄牙總理,下令派飛機參與了這場非法入侵,完全繞開聯合國,這就是一場純粹的犯罪式轟炸,沒什麼國際法撐腰,只有強權邏輯。
我也寫過書討論這個問題,至今我還在想真實原因是什麼。我覺得在這個危機中,最重要的是德國的行為,其次是美國,然後才是英國。如果我們分析南聯盟的危機,以及此前肢解南聯盟的行為,就能看到不同國家在利益和側重點上的變化與轉換。
我以前有機會跟米洛舍維奇聊過,我是他的直接合作方,當然也接觸過所有那些參與過危機的人——從1991年、1992年開始直接參與的那批人,在掌握情報的高層核心人員中,當時南聯盟軍方和軍方情報部門高層認為轟炸和擠壓塞族背後的幕後推手是德國。
可能俾斯麥是德國最後一個主張跟塞族和平協商解決問題的真正領袖,歷史上俾斯麥不願意跟塞爾維亞打仗,但到了奧匈帝國時期事情就變了,德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跟塞族站在了對立面,二戰時納粹德國除了在克羅地亞對塞族搞種族屠殺,甚至在塞爾維亞本土也發生了這樣的慘案。從克拉古耶瓦茨開始,到各個城市都出現過對塞族的屠殺,貝爾格萊德、米特羅維查這些地方都有。
到轟炸南聯盟的時候,德軍也派飛機轟炸了南聯盟本土,包括把科索沃從塞爾維亞搶走的一系列行為中,德國親自全面參與。最近,德國對塞爾維亞施加的最大壓力就是此前的德法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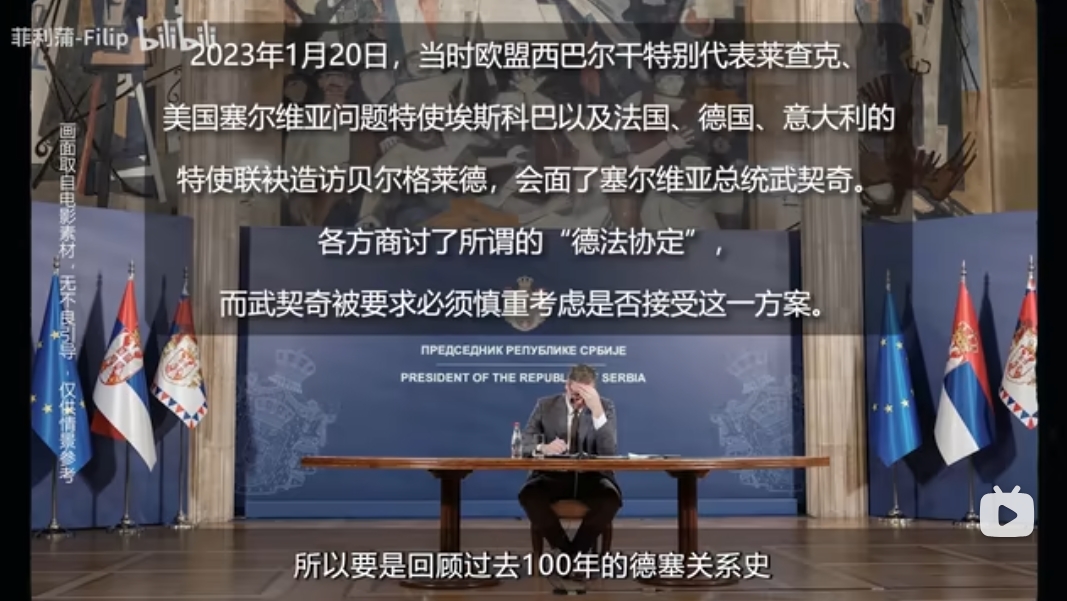
所以如果回顧過去100年的德塞關係史,德國一直想方設法讓塞爾維亞的國土面積越來越小,讓塞爾維亞的勢力範圍越來越小;他們還一直試着讓德國官員去指揮、領導塞爾維亞的政治進程,比如在波黑塞族共和國就有個德國高級代表,過去那些波黑高級代表好歹還得走合法程序才能頒佈法律,得讓議會接受這種立法,不管是靠施壓、威脅或是其他手段。施密特(波黑高級代表)自己寫了一整套立法,頒佈後把自己定義成立法者。他在德國也是一個失敗的政客,以前當過國防部長/農業部長,以及其他部門的助理,現在是準退休官員,私底下就這麼推動立法。而在他背後是柏林的激進反塞政策,這是整起事件的第一個維度。
第二個維度是德國花了很大力氣去調動其他國家。1990年代是美國的時代,先是信息革命,再加上他們的軍事實力,尤其海灣戰爭後基本上所有西方國家都圍着美國轉。在沒有同外部協商的情況下,北約開始了東擴。信息革命還給美國提供了大概十年的經濟發展窗口,而在全球議題層面,信息革命成了西方政治觀念向海外傳播的重要工具,也就是他們的全球自由主義或者自由全球主義,美國靠這個成為全球單極。
在此背景下,德國作為一個經濟巨頭也靠向了美國,開始跟美國聯手搞了一系列反塞政策。我手上沒什麼直接證據,但我們軍方部門能證實。德國方面出資支持過克林頓家族等其他美國家族,為了推動自己的一系列地緣政治政策,尤其是針對巴爾幹的政策。
**菲利蒲:**那我們能不能認為是德國遊説了美國,讓美國對南斯拉夫採取更激進的政策?
**格蘭·馬蒂奇:**我跟你講個事情,大概2010年的時候,我因為私人工作原因去了一趟俄羅斯,那時候我已經不搞政治了,到那裏後有一個我從沒見過的人接待了我——我知道他的存在,但沒見過,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我去了俄羅斯的。這個人當時應該是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的顧問,負責巴爾幹事務,以前在南聯盟解體期間當過總參謀長,叫卡迪耶維奇。他住在莫斯科,説要給我傳個信息,這個信息他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分享,因為他不怎麼離開莫斯科。
我們聊了五個多小時,整個對話的核心就是,他説,你記着,塞爾維亞在這個世界上跟阿爾巴尼亞族、克羅地亞族不完全是敵對的,當然總歸有激進分子,但民間其實沒有、也不該有這種情緒,甚至美國、克羅地亞都不算我們的敵人,我們的對手是德國,所有那些想肢解塞族的當地勢力——不管是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還是克羅地亞的烏斯塔沙右翼勢力,還是其他一些國家搞的奇奇怪怪政策,以及那些在南聯盟期間行為詭異、對塞族立場特別不友好的國家,比如現在歐盟中的斯洛文尼亞,他們都不過是德國的代理人,他們只有在德國下指令的時候才會出現特別反塞爾維亞的政策,如果沒有德國,他們都能跟塞爾維亞做朋友,大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這就是已故的維爾科·卡迪耶維奇的立場。

我想他掌握的信息,甚至比當下我們國家的情報部門還多。鐵托時期,南斯拉夫曾有過世界級的情報部門,跟中國也有過非常友好的合作,跟全球各個國家關係都不錯。前南地區的危機,如果德國沒有把自己的利益摻雜進去,可能整個情況會很不一樣。這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德國形成的地緣戰略,至今仍在推動這樣的戰略,他們稱之為“向東南方向的滲透”,其地緣維度的核心考量,是達到巴爾幹、達到亞得里亞海的温水海域,以及到克羅地亞這一大塊區域。而塞爾維亞是他們最大的攔路虎,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核心問題。
**菲利蒲:**説到西方的亂子,我們能看到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內部都有點亂;但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穩定。而且,因為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反對派等等,以及西方的影響力——我指的是文化上的影響,從1990年代到2000年後滲透到塞爾維亞的西方影響力。您怎麼看目前塞爾維亞的情況?
**格蘭·馬蒂奇:**從歷史比較分析看,西方世界現在有點像歐洲進入現代政治前的樣子。我寫了兩本書,裏面有做具體分析,馬上就要發表了。我對比了16世紀和現在西方的處境,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什麼?社會政治轉型、法制轉型、地緣政治關係的轉型……十年後的世界跟現在會完全不一樣,地緣政治關係會有大變化,甚至國家政體都可能會變,很多事都會變,這些過程永遠帶着痛苦。可惜的是,該負責的人往往不是付出代價的人,這是個特別混亂的過程。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的情況,他們有一些新的地緣政治考量,如果真能把美國國際開發署取消或者至少限制它的活動,如果真能關掉自由歐洲電台或美國之聲——自由歐洲電台就在我布拉格的家附近,總部離我一公里,那不是一棟樓,而是一個建築羣,您明白嗎?這是個媒體帝國,他們資源多得嚇人,有一堆記者,跟各種媒體都有聯繫,甚至我們都不知道他們跟誰有關係,這是遠超媒體的機構,天曉得未來會怎麼樣。
關鍵變化是以後不會有單極,也不會有一個“教宗”在那兒天天嚷嚷着指揮你,就像16世紀馬丁·路德來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大變,所以從這個亂局裏面會冒出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權力格局和全球秩序。
特朗普會往哪走我不知道,現在很難有人告訴你特朗普會怎麼樣,比如我們看俄羅斯哲學家杜金的發言,他説特朗普背後的深層政府比傳統認知中的深層政府還深,他們意識到原來的體制基本沒什麼利益了,就又把特朗普推出來,但這背後肯定有一個系統在支撐,這個系統有自己的利益,我們未必完全清楚,但確定的是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歐洲服軟、服從的心態要沒了。
特朗普上台那天,朔爾茨在德國失勢,接着葡萄牙總理下台,歐洲會有多米諾骨牌效應,那些歐洲政府就是自由主義世界代理機構,其核心代理象徵曾經是拜登,但他也不是核心領導者。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保持理性,就像剛説的塞爾維亞作為國家存在,核心競爭對手還是德國;英國的利益我們有時不太懂,但對我們造成的傷害沒有德國大,關鍵在於特朗普跟德國在巴爾幹問題上會談成什麼利益,以及未來俄烏戰爭的談判,在烏克蘭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我們要看看其他問題是否會被順帶解決。

當地時間2月18日,俄美兩國代表團在沙特利雅得就俄烏戰爭問題舉行會談。 央視
現在分析人士認為,甚至我有些朋友也跟我説,從去年10月開始美俄軍事高層就在瑞士接觸了,討論瞭如何解決烏克蘭問題,還聊了其他問題。我作為塞爾維亞人,關心的是塞爾維亞問題在哪兒?會被放進哪個談判桌?會被放進各種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談判裏嗎?比如俄羅斯會説我們在幾天內拋棄了阿薩德和敍利亞,要不你們拋棄那邊,我們再拋棄這邊,諸如此類的。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最後會談成什麼,但毫無疑問我們得維持愛國主義戰線的統一;塞爾維亞到底有沒有民眾間的統一?只有統一了才能塑造護城河,擋住各種對我們不利的地緣政治舉措。如果不統一,就會有人亂搞。

當地時間3月11日,小唐納德·特朗普與武契奇會面。 “X”
不幸的是,現在有學生遊行等一系列事情。我寫過“顏色革命”相關的書籍,有些人你可能比我還熟,但凡瞭解顏色革命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是自發的,我不信這是突然自發的巧合的社會現象,社會活動裏很少有純粹自發的東西。
法國學者勒龐寫過一本很經典的書,19世紀末的《烏合之眾》,所有跟羣眾打交道的領導者肯定會看。這本書裏面論證的理論在我們國家也有出現,甚至不僅是理論,還有操縱羣眾的各種手法都實踐了,就是一套操縱民眾反體制的行為。
但遺憾的是,塞爾維亞現在的情況,是政府給了太多理由讓這種抗議規模越來越大,這是核心問題。作為塞爾維亞公民,雖然我目前不住在塞爾維亞,但我得承認學生提的部分訴求確實有依據,他們説國內有腐敗,而且腐敗直達高層,他們沒説錯,他們希望這種情況能被有效處理。
目前對塞爾維亞來説,腐敗是最大的內部風險,遠超外部。我覺得武契奇總統犯了些錯誤,四個月前剛開始時,他應該用更多情緒和時間對付這個問題,滿足一些訴求,然後把反腐指向自己圈內的人,而不是三四層外的官員,尤其是他們黨內的人。從我的角度看,我也認識武契奇本人,我覺得武契奇現在處境挺難的,他看起來像是自己圈子的人質,因為這些人的存在武契奇沒法全力滿足學生的訴求——我指的是那些有道理的訴求,什麼過渡政府、技術政府都是胡扯——抱歉我用了“胡扯”這詞,但這些訴求跟民主法制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現在體制下,政府得通過議會確認和授權,要是議會確認不了,那就重新選舉,選出新議會、新政府。就像馬其頓以前有過的過渡政府,敍利亞上台了一個曾經的“恐怖分子”,現在拍着胸脯説我是總統了,這叫民主嗎?塞爾維亞不會有這樣的劇本。塞爾維亞還是有國家傳統的,至少比這些國家的傳統深遠,尤其比馬其頓深厚。

在塞爾維亞,沒法靠暴力上台,除了2000年那次“顏色革命”。我覺得武契奇需要改變對自己圈子的態度,好好跟學生談,滿足他們那些有道理的訴求,因為這些訴求背後不只是學生,還有很多不滿的羣眾。我覺得武契奇應該拿起棒子、掃帚身邊的一些人清理掉,這樣才能把權威還給機構,也還給自己。目前學生不是要武契奇辭職,而是希望武契奇按憲法賦予的權力做事,讓系統發揮作用,這樣那些具有“顏色革命”要素的行為體也會被卸下武裝,因為他們會失去煽動羣眾顛覆國家的抓手。
目前塞爾維亞的情況在世界上也少見,學生同時對執政黨和反對派不滿,甚至對反對派更不滿,這是新現象。可能歐洲國家此後也會陸陸續續出現這樣的情況,捷克5月初會有一個大規模遊行,可能有20萬人參加。在歐洲,我們會看到大批不滿羣眾上街,希望看到新面孔、新規則、新政治、新的價值和道德。
聊到塞爾維亞的腐敗,這不是塞爾維亞獨有的,是從歐盟及西方國家那兒得到的。我們甚至能看到馮德萊恩發短信跟輝瑞這些大企業談鉅額利益,布魯塞爾乾的事簡直不可想象。如果未來時代更理性,布魯塞爾現在乾的事情肯定會被記住的。
菲利蒲:非常感謝您的分享,希望我們近期還會再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