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人不再搬家了?——彭博社
Shawn Donnan
 插圖:Tomoko Mizuno為彭博社創作
插圖:Tomoko Mizuno為彭博社創作
美國人究竟是’被困住’還是樂居故土?(音頻)
8分03秒
美國長期以來的重大經濟優勢之一,是其作為機遇之地的形象。這幫助全球最大經濟體吸引人才並催生創新。最佳狀態下,美國是一台建立在流動性和精英制度上的財富機器。
但這終究是個神話。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美國正淪為機遇遞減的國度。機會分配不均,財富被少數人壟斷——他們從偏向富人的税收、教育和住房政策中獲取超額收益。這個國家對新移民也日漸排斥。
《大西洋月刊》編輯Yoni Appelbaum在其新書*《困局》*(蘭登書屋,2月18日出版)中提出了另一個佐證:美國人不再像19世紀至20世紀初那樣,為追尋機遇而進行地理遷移。
*《困局》*深刻剖析了這個曾讓人民自由遷徙、追逐更好生活的國家,如何逐步扼殺了流動性。書中將分區制度及地方政府自19世紀以來對此的推崇列為首要癥結,正是這些因素使美國淪為排他性社區的集合體,加劇了不平等。
阿普爾鮑姆以記者為業,但本書更像一部可讀性強的歷史著作——這很合理,因為他加入《大西洋月刊》前曾是擁有博士頭銜的歷史學者。相較於剖析當代住房政策辯論或近期移民趨勢,他用了更多篇幅追溯美國殖民時期以來管控境內人口流動的種種嘗試。
例如我們瞭解到,自1690年起長達一個多世紀裏,馬薩諸塞州戴德姆鎮禁止可能成為社區負擔的新居民入住,包括現有居民的僱工和租客;瞭解到分區制度誕生於19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初衷是控制華人移民開設洗衣店的位置;還了解到1930年代加州曾派警力駐守州界阻攔經濟移民——這些移民並非來自墨西哥,而是美國其他州。
阿普爾鮑姆記錄了紐約市因所謂"廉租公寓恐懼症"掀起的區劃浪潮,講述了城市規劃專家簡·雅各布斯如何推動西村區開發限制,反而加速了該地區的高端化進程。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他追蹤了分區制度如何限制大遷徙時期遷入的非裔家庭通過流動獲取經濟收益,以及當地產業空心化如何使許多人陷入困境。
全書始終頌揚着移民為追求更好生活而流動的個人故事,但《困局》的核心論點——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美國是流動自由的黃金國度——與作者鋪陳的史實存在矛盾。幾乎每個案例都以某人或其後代遭遇制度性機會壁壘告終。宏觀來看,這個國家始終對 newcomers 抱有戒心,即便發展始終依賴他們。本書更深刻揭示:美國人面臨的流動障礙,與合眾國歷史同樣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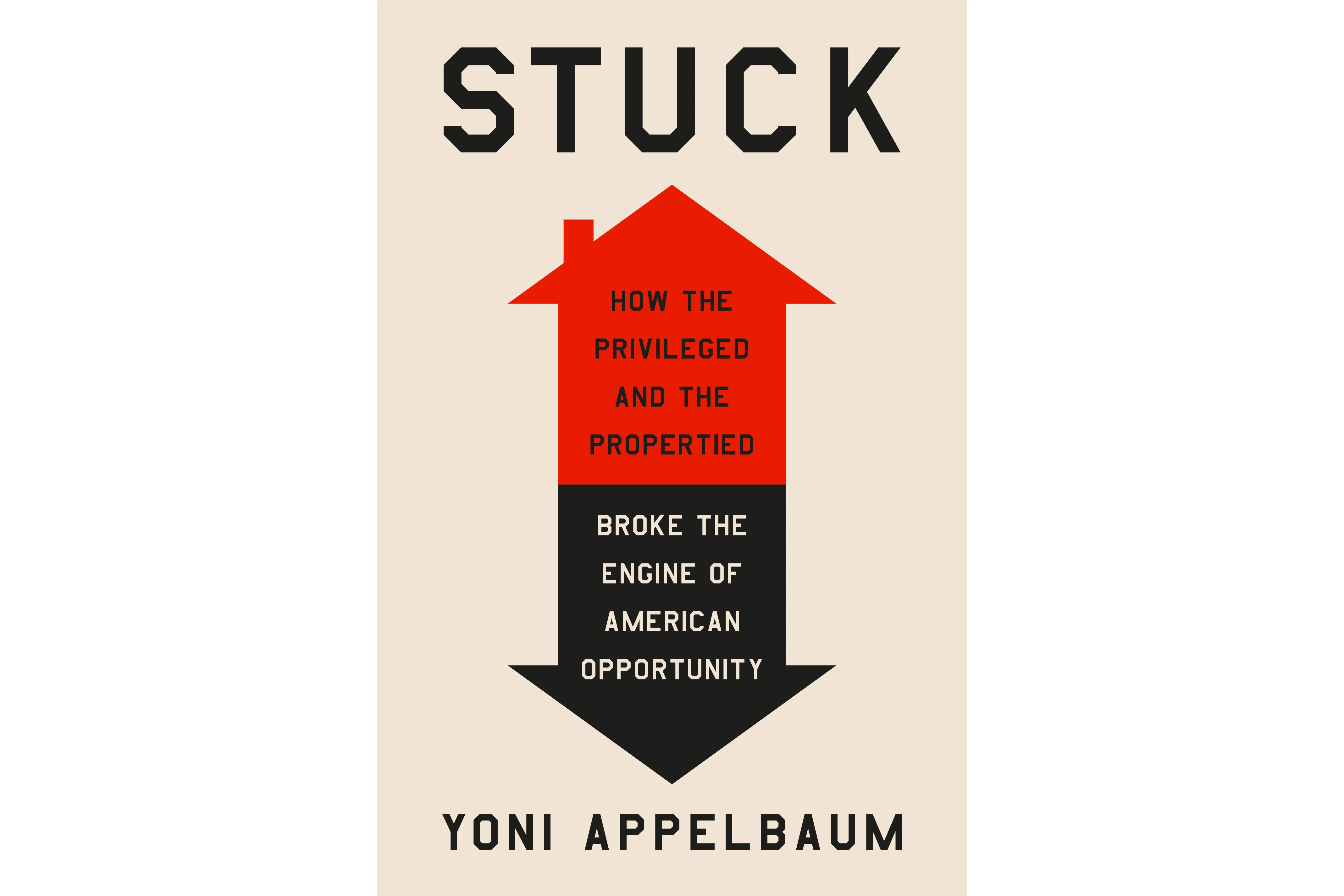 儘管阿佩爾鮑姆的書流暢地闡述了美國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但對當代美國的着墨較少。當他談及當下時,往往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且對機遇所在的看法顯得狹隘。
儘管阿佩爾鮑姆的書流暢地闡述了美國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但對當代美國的着墨較少。當他談及當下時,往往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且對機遇所在的看法顯得狹隘。
阿佩爾鮑姆在波士頓郊區長大,他在書中開篇就哀嘆自己的年輕家庭無力在類似環境中生活。後來他揭露了華盛頓特區同齡人的虛偽:先是那位在草坪上豎起對立標語的鄰居——一邊寫着"無論你來自何方都歡迎",另一邊卻呼籲路人向安置移民的新公寓樓"説不";再是馬里蘭州塔科馬公園這個進步主義郊區,當地居民花了數十年阻撓將通勤者停車場改建為經濟適用公寓的計劃。
在這些案例中,阿佩爾鮑姆用美國特權階層的角落來詮釋他所見的全國性機遇壁壘。他似乎在論證: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紐約、舊金山或首都精英社區的生活,這是國家的恥辱。
但這些地方與美國更廣泛的社會流動圖景鮮有共通之處。這種流動也出現在亞特蘭大和夏洛特等城市——它們正吸引新一代黑人重返南方,逆轉了20世紀"大遷徙"中祖輩為逃離種族隔離、追尋弗林特等城市工廠工作而北上的歷史軌跡。
阿佩爾鮑姆同樣沒有談及工作形態的變遷現實:互聯網意味着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追求新職業。我認識一些人,他們近年來分別向懷俄明州和意大利的老闆遠程彙報,也有人足不出户就在家庭辦公室管理着東歐、印度和摩洛哥的建築師、會計師和軟件工程師團隊。如今我們遷移減少,部分原因或許是我們已不再需要遷徙。
當然,這些都屬於白領階層的案例,而阿佩爾鮑姆部分想指出的是當代人口流動的不平等性。他寫道:“美國工人階級曾是最能從遷移中獲益的羣體,如今這已成為主要由富裕階層行使的特權。”
為佐證這一觀點,他舉例説明律師和清潔工從美國深南部遷往紐約的差異——與1960年相比,如今清潔工的處境會糟糕得多。這個假設會讓布魯克林的讀者會心點頭,但在當今經濟環境下,現實情況更可能是律師和清潔工都更傾向於從紐約遷往亞特蘭大或納什維爾。
 內華達州里諾市正在建設的新住宅。攝影師:艾米麗·納傑拉/彭博社《困局》一書以及關於移民的政治討論中,還缺失了一些歷史背景:世界上大多數人其實不願遷徙。人類是追求安逸的生物,移民到另一個國家或州意味着要離開家人和社交網絡。遷移往往是人們被迫而非主動選擇的行為。
內華達州里諾市正在建設的新住宅。攝影師:艾米麗·納傑拉/彭博社《困局》一書以及關於移民的政治討論中,還缺失了一些歷史背景:世界上大多數人其實不願遷徙。人類是追求安逸的生物,移民到另一個國家或州意味着要離開家人和社交網絡。遷移往往是人們被迫而非主動選擇的行為。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2023年美國僅有450萬1歲及以上人口遷往其他州。這與1948年的440萬人大致相當,儘管當時的總人口要少得多。更令人驚訝的是:在2023年和1948年,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搬家。2023年,92%的美國人口留在原居住地,這確實創下了歷史新高。1948年,這一比例為80%。即便如此,當時也只有3%的人口遷往其他州。
所有這些都揭示了一個關於人性和個人生活進程的、令人不安的真相,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是一個出生在加拿大的澳大利亞人,生活在美國,並與一位美國公民結婚。我告訴自己,我也是一個生來就漂泊不定的人,父母也是遊歷四方的人,因此基因裏就帶着不安分。我從小每隔幾年就跨越國界搬家,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以體驗為名——當然也帶着一些野心——更換國家、城市和住所。我們已成年的兒子在三個不同的國家慶祝了他的前三歲生日。我們的女兒在我們從香港搬到倫敦後不久就在那裏出生。
然而最近,我和我的家人在同一棟郊區房子裏住了十年。我並沒有放棄冒險或經濟機會。我預計還會再次搬家。但事實是,隨着年齡的增長和孩子的到來,搬家的難度增加,這也削弱了搬家的意願。作為父母,你開始更關注那些重視童年穩定性的心理學家,而不是那些鼓吹流動性的經濟好處的經濟學家。此外,我對流動性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人類搬家,往往只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停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