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會拖延?對一些人來説,這意味着用自己的方式工作 - 彭博社
Anna Holmes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這個故事是《彭博商業週刊》的特別報道之一。更多內容請點擊這裏。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這個故事是《彭博商業週刊》的特別報道之一。更多內容請點擊這裏。
我最初是懷着最好的意圖開始的。坐在沙發上,電腦放在腿上,我開始打字,然後又打了一些字。抬頭看到房間對面的情況有點亂,尤其是地板上堆放着一堆書,我買來作為我試圖寫的書的素材。我站起來把它們整理成更整齊的樣子。然後貓在窗邊開始哭。我又站起來。原來它想要打開百葉窗,這樣它就可以坐在陽光下。我打開了百葉窗。我重新坐下。現在我決定我渴了。但是放在腳下咖啡桌上的一杯番石榴味的LaCroix已經失去了氣泡…而且裏面還漂浮着貓毛。我站起來打開了一罐新的。在廚房裏,我查看了我的Fitbit:到目前為止走了459步——在一個600平方英尺的公寓裏。按照這個速度,到下午1點我會走一千步。而現在才早上10點。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上一段是我嘗試致敬英國作家傑夫·戴爾(Geoff Dyer)的——具體來説是他1997年出版的精彩著作《純屬憤怒》,這本書記錄了他試圖(以及失敗、分心和轉移注意力)寫一本關於D.H.勞倫斯的學術著作。戴爾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來逃避寫作。他需要更多的報告,需要多做筆記。他不確定自己想住在哪裏。在哪個歐洲城市他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書開始時,他在巴黎,考慮加入他的伴侶在羅馬的生活。然後他飛往希臘度假,這並沒有幫助解決問題。)他研究雷納·瑪利亞·里爾克的作品,深信“更好地理解里爾克對我理解勞倫斯至關重要。”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上一段是我嘗試致敬英國作家傑夫·戴爾(Geoff Dyer)的——具體來説是他1997年出版的精彩著作《純屬憤怒》,這本書記錄了他試圖(以及失敗、分心和轉移注意力)寫一本關於D.H.勞倫斯的學術著作。戴爾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來逃避寫作。他需要更多的報告,需要多做筆記。他不確定自己想住在哪裏。在哪個歐洲城市他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書開始時,他在巴黎,考慮加入他的伴侶在羅馬的生活。然後他飛往希臘度假,這並沒有幫助解決問題。)他研究雷納·瑪利亞·里爾克的作品,深信“更好地理解里爾克對我理解勞倫斯至關重要。”
矛盾的是,他的散文自信而迅猛,表明他並不太在寫作上掙扎。此外,在他一本書的早期頁面上,在標題“Geoff Dyer的其他作品”下,他的出版商列出了他寫的其他10本書。十本!到目前為止,我只寫了兩本書,而那些只是選集和彙編,不是原創敍事,我想原創敍事比我接手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難和存在挑戰性。直到現在。
我很清楚,我並不是唯一一個——或者説,也不是唯一一個作家——偶爾會遭受無法完成事情的痛苦,有時甚至是病態的。很多作家討厭寫作這個行為。憎惡它。他們有不同的方法來應對這種感覺。有些人散步。抽煙。或者喝酒。當她感到不知所措時,一個朋友使用番茄工作法,設置一個25分鐘的計時器,將任務分解成可管理的部分,這樣她可以更容易地完成。另一個朋友,Jami Attenberg,即將出版一本名為1000 Words的面向作家的書,副標題是“作家的指南:全年保持創造力、專注力和高效率”。我打算給朋友買幾本。
拖延(以及由此導致的缺乏生產力)給經濟造成了損失——蓋洛普測算出全球“不投入工作的員工”每年造成的成本為7.8萬億美元。拖延會帶來明顯的個人成本。根據2023年的一項研究,它可能會對你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由於這是一個如此普遍的問題,無論是對作家還是對普通人,都有一個專門的市場致力於幫助人們提高生產力,一種生產力工業複合體。數十本,甚至數百本書,更不用説視頻教程、應用程序和網站可以下載和查看或玩耍,都在爭奪那些拖延工作的人的注意力。研究人員表示,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工作日用於實際工作。當不在(通常是表演性的)會議中時,人們可能會想象一些時間用於通過拖延來避開令人不愉快且必要的任務。有人可以僱傭來幫助你提高生產力;還有整個貿易協會致力於生產力和組織諮詢領域。還有像Tim Urban這樣的生產力大師,他的TED演講“一個拖延狂的思維內部”已經有6700萬次觀看次數且還在增加。
顯然,這是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行業,我不想參與其中。誰願意下載應用程序,聽播客,支付顧問費,學習荒謬複雜的日記技巧,總的來説,在很難完成“真正”的工作的情況下花更多的錢呢?
但是,我的書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要交稿了,我寫了大約25,000字,而我希望寫的是這個數量的四倍。我需要一些幫助。所以我決定做我知道自己擅長的一件事,閲讀書籍,既能理解自己的拖延行為,又能在與其他拖延者一起感到稍微不那麼孤獨。
 插圖:Sam Wood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奇怪的是,我目前的情況相當新穎。多年來,我一直是一名作家和編輯,之前還有兩本書問世。一本是關於女性分手信的文化史;另一本是一本百科全書,受到我創建的名為Jezebel的網站觀點的影響。我沒有拖延這些書,老實説,我不太清楚為什麼。一個想法:隨着我成為一名更有經驗的作家,我也變得更加不安全,被一種在年輕時沒有的冒名頂替綜合症所束縛。 (稍後詳談。)另一個:我只是變得更老和更懶。第三個:該死的互聯網的干擾。
插圖:Sam Wood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奇怪的是,我目前的情況相當新穎。多年來,我一直是一名作家和編輯,之前還有兩本書問世。一本是關於女性分手信的文化史;另一本是一本百科全書,受到我創建的名為Jezebel的網站觀點的影響。我沒有拖延這些書,老實説,我不太清楚為什麼。一個想法:隨着我成為一名更有經驗的作家,我也變得更加不安全,被一種在年輕時沒有的冒名頂替綜合症所束縛。 (稍後詳談。)另一個:我只是變得更老和更懶。第三個:該死的互聯網的干擾。
這個項目也是我承擔的一種不同類型的工作。我可以向學員和其他人強調,恐懼是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我們需要做那些讓我們感到害怕和挑戰的事情,才能在事業和其他方面取得進步和上升。但是獨自寫書的工作讓我感覺自己像是在快速沙漠中掙扎。在我職業生涯的其他時候,例如當我為一個更大的實體擔任編輯,並且還有一個辦公室工作時,我沒有拖延的問題。事實上,以前的同事可能會説我有過度工作的問題,經常對我的健康和個人關係造成損害。
現在?有人可能會説我正在過着夢想般的生活。我可以在家工作。自己安排工作時間。決定何時洗澡。 (通常我會洗。)但作為編輯、創意總監或製片人與創意型人才合作是一回事。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出視線,幫助其他人閃耀。寫作,尤其是寫書,是另一回事。首先,我的名字會出現在封面上。我還有經濟責任——其中很多是對我的父母,他們從未賺過多少錢——這些責任令人難以承受,而且短期內不會改變。而且,無結構的時間和內在壓力要制定一個固定的時間表,讓我以前從未有過的方式來評判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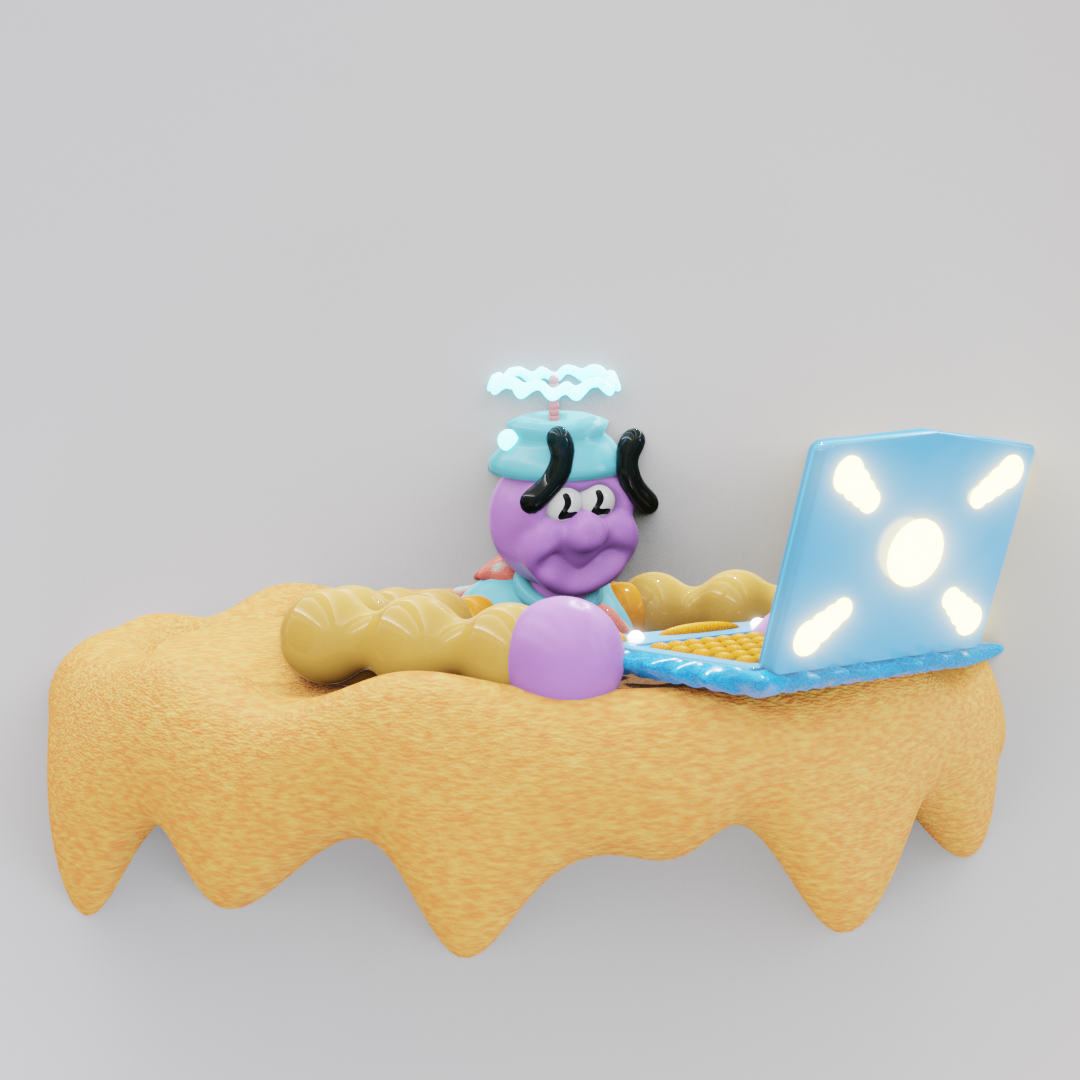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我的新書的主題是我不想談論的事情。從一對新書中我學到,不談論它,是從凱瑟琳·摩根·施弗勒(Katherine Morgan Schafler)的《完美主義者的失控指南》和托馬斯·柯蘭(Thomas Curran)的《完美主義陷阱:擁抱足夠好的力量》中學到的,這是一種完美主義,一種控制似乎失控情況的方法。畢竟,如果我不告訴別人我在做什麼,那麼它的不可避免的失敗——或者甚至是我無法完成它——將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至於完美主義,根據柯蘭這樣的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以及心理治療師施弗勒的説法,它是拖延的根源,如果不是根本原因。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我的新書的主題是我不想談論的事情。從一對新書中我學到,不談論它,是從凱瑟琳·摩根·施弗勒(Katherine Morgan Schafler)的《完美主義者的失控指南》和托馬斯·柯蘭(Thomas Curran)的《完美主義陷阱:擁抱足夠好的力量》中學到的,這是一種完美主義,一種控制似乎失控情況的方法。畢竟,如果我不告訴別人我在做什麼,那麼它的不可避免的失敗——或者甚至是我無法完成它——將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至於完美主義,根據柯蘭這樣的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以及心理治療師施弗勒的説法,它是拖延的根源,如果不是根本原因。
Schafler的書以一個簡短的測驗開始,幫助讀者確定他們屬於五種完美主義者中的哪一種。我參加了測驗,很快發現自己一半是巴黎完美主義者(具有強大的同理心和與他人建立緊密聯繫的強烈願望),一半是凌亂完美主義者(一個“超級創意生成者”,不能始終專注於目標)。奇怪的是,我顯然不是拖延狂完美主義者,這種類型的人經常反芻,預期失敗,淡化自己的成功,開始任務時會“等待條件完美才開始”。這對我來説感覺不公平,除了等待條件完美才開始。我絕對不會這樣做。但反芻和其他一切呢?經典。為了超越他們身份的這一方面,Schafler建議拖延狂完美主義者“與支持者結盟”。這既有點模糊,又違背了我在感到害怕和困惑時通常會做的事情,那就是躲在某個角落裏,是的,反芻。
《完美陷阱》中沒有測驗,這本書強烈主張拖延是完美主義的症狀。正如Curran指出的那樣,“完美主義者將拖延作為一種在沒有必然情感傷害的情況下度過掙扎、挑戰和失敗的方式。”當我在七月中旬通過電話與Curran交談時——一開始電話打不通,這讓我感到一種奇怪的寬慰——他將拖延描述為情緒調節問題,而不是時間管理問題。
情緒調節,意味着練習並掌握對困難情緒狀態的控制,這是我幾年來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我的治療師作為認知行為療法課程的一部分,敦促我在感到焦慮或不安時“觀察和描述”。她説這既可以讓我平靜下來,也可以處理我的情緒。但當我拖延時,我感到無法完全觀察或描述任何事情,因為我感到的是徹底的、壓倒性的羞恥。一位知名的TikTok博主@neuroqueercoach也提供了類似的建議,向她的粉絲解釋説拖延是一種“我們可以通過意識到我們拖延時的情緒來改變的習慣。”但至少對我來説,觀察和描述似乎會促使我感到更多的羞恥,然後導致更多的恐懼、厭惡,毫不奇怪,更多的拖延。
對於我自己大腦之外的人來説,“羞恥”可能感覺有點言過其實。有點太戲劇化了。然而,它似乎也是恰當的。柯蘭本人毫不猶豫地使用這個詞。在他的書中,這位自稱完美主義者早早地解釋説,他的治療師“能夠向我展示,我正在遭受深刻的自我厭惡、羞恥和悲傷,這些情緒被我的完美主義者身份巧妙地掩蓋和加劇。”在我與他的通話中,柯蘭説完美主義者發現很難處理失敗,並與“強烈需要他人認可”的情緒鬥爭,這導致了深深的羞恥感。當事情變得困難或當他們面臨他們確信會失敗的任務時,他們會退縮、反芻並參與“自我破壞”的拖延。這是一種焦慮管理技術——正如柯蘭所説的“非常強大的材料”。而且真的很糟糕。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雖然柯蘭(以及紐約時報)強調拖延是關於情緒,而不是時間管理,但我並不急於否認這個想法,即它並沒有受到現代時間壓力的深刻影響。時間是珍妮·奧德爾(Jenny Odell)精彩新書《 拯救時間:發現時鐘之外的生活》的主題。巧合的是,正是在我將那個代表優化的硅谷標誌,一隻蘋果手錶,綁在左手腕的時候,這本書到手了。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山姆·伍德雖然柯蘭(以及紐約時報)強調拖延是關於情緒,而不是時間管理,但我並不急於否認這個想法,即它並沒有受到現代時間壓力的深刻影響。時間是珍妮·奧德爾(Jenny Odell)精彩新書《 拯救時間:發現時鐘之外的生活》的主題。巧合的是,正是在我將那個代表優化的硅谷標誌,一隻蘋果手錶,綁在左手腕的時候,這本書到手了。
奧德爾認為,現代時間觀念與工資勞動、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現實密不可分,這反過來又影響了我們對於人類意義的看法。這似乎與我身上戴着的設備的用意背道而馳,因為它可以顯示互聯網時間、温度和日期。(更不用説它計算從我的血氧水平到我從坐姿站起的頻率的一切。“該站起來了!”它歡快地宣佈。)
更多來自商業週刊的特別報道:
我對此感到奇怪。不僅僅是因為我購買了我實際上不需要的東西,尤其是在看着我的預付款減少時感覺自己在花錢。 (我安慰自己,我的蘋果付款計劃讓我每月只花費32美元。)也不是因為購物本身就是一種拖延或情緒逃避的形式。而是因為,正如奧德爾指出的那樣,特定時間點的概念和規範(她稱之為“時間單位”)是一個相當近期的現象,源自於,並且使時間被視為金錢的想法得到了實體化和強化;一種可以量化、利用的東西。這也非常白人化。奧德爾引用了學者布里特尼·庫珀(Brittney Cooper)2017年的TED演講,“時間的種族政治”,這是對庫珀解釋的“權力者如何規定工作日的節奏…他們規定我們的時間實際價值有多少錢”的引人入勝的探索。
奧德爾的書沒有涉及拖延。至少不是明確地。但它也沒有必要。正如她所指出的,我們將時間用作繁忙程度的衡量標準,也被用作衡量誰和什麼是“好”的標準,誰“贏了”或“壓倒了”的標準。我意識到,我的蘋果手錶只是另一種主要用途是測量我如何使用或不使用我的時間,計算我在生活遊戲中表現如何的設備。我想起了書中的一個早期部分,奧德爾在日記中分享了她的思考,特別是她在從東灣到舊金山半島的汽車上的觀察。 “在綠燈亮之前,我低頭看着我的手機,它在舊杯架裏格格不入,”她寫道。“一個伴侶,是的,但也是一個衡量生活的設備。”
奧德爾特別痛恨自助和時間管理書籍,以及她所稱之為“生產力兄弟”,這些平凡無奇的傢伙們具有“自我掌控的修辭,為YouTube和Instagram時代重新打造而成”。當你尋求克服拖延的幫助時,你可能會遇到這些生產力兄弟,像Urban這樣的人,他將2016年的TED演講轉化為更多關於拖延和生產力的內容,以及亞當·格蘭特,一位組織心理學家和TED的同行,他有五本暢銷書籍涉及拖延相關主題,比如動機。互聯網的大片區域被那些給出生產力建議的男性佔領了——如何崛起和奮鬥,保持努力,永遠不要讓目標離眼前,保持專注。他們只痴迷於一件事,那就是不浪費時間。
奧德爾提到的另一個人是克雷格·巴蘭丁,他自稱為“世界上最有紀律的人”,2015年幾乎在凌晨4點起牀工作,寫作了他的著作完美的一天公式:如何擁有美好的一天並掌控你的生活。凌晨四點!
我決定我討厭克雷格·巴蘭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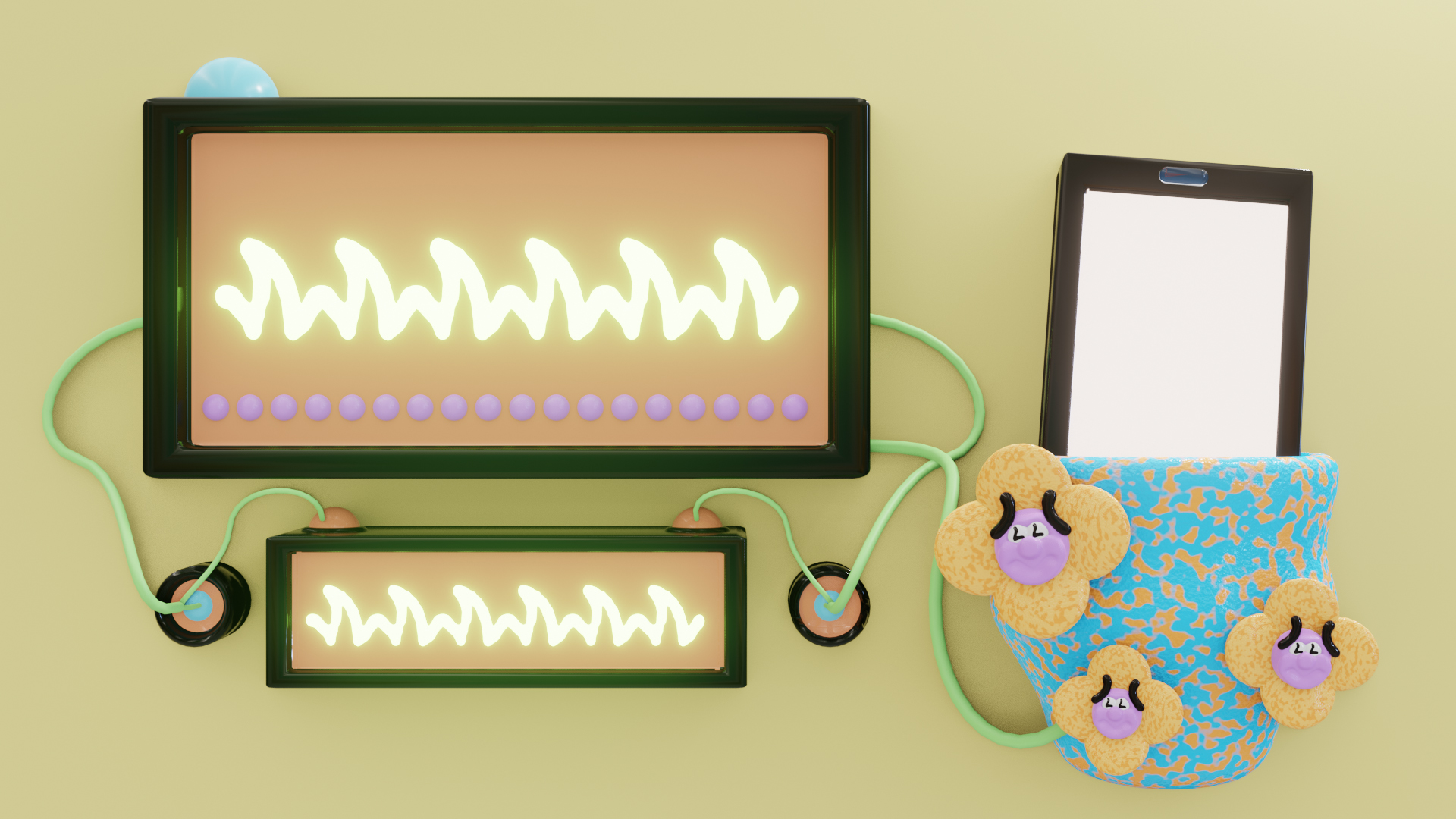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薩姆·伍德我有時會思考完美主義與性別和種族巨大壓力之間的聯繫。對於許多歷史上被邊緣化的人羣來説,成為“最好的”——或者比最好的更好——是獲得機會的先決條件。2018年,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完全披露:我曾為她的製作公司Higher Ground工作)在她的超級暢銷書籍 成為中提到,“你必須做到比別人好一倍才能走得更遠。” 奧巴馬本人也在回應黑人美國人之間經常表達的觀念,即他們必須做到比白人同行更優秀才能獲得更容易被我們白人同行享有的職業利益和尊重。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薩姆·伍德我有時會思考完美主義與性別和種族巨大壓力之間的聯繫。對於許多歷史上被邊緣化的人羣來説,成為“最好的”——或者比最好的更好——是獲得機會的先決條件。2018年,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完全披露:我曾為她的製作公司Higher Ground工作)在她的超級暢銷書籍 成為中提到,“你必須做到比別人好一倍才能走得更遠。” 奧巴馬本人也在回應黑人美國人之間經常表達的觀念,即他們必須做到比白人同行更優秀才能獲得更容易被我們白人同行享有的職業利益和尊重。
這種壓力是我能夠理解的,作為一個來自中下層家庭的黑人,也是一個女性。多虧了我家鄉的公立學校系統,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我也很早就意識到,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特別是在紐約媒體的白人和男性主導的常春藤聯盟領域,我必須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專注和強度。我需要假裝直到成功。
柯蘭(Curran)也在一箇中下層家庭的環境中長大,並且通過大量的努力和辛勤工作,一步步攀上了學術階梯。儘管他的書並沒有深入探討種族和性別在完美主義中的作用(也許作為一個白人男性,他不是合適的人選),但他談到了階級,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階級。“當然,我自己與完美主義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一種需要過度成就,以彌補社會和經濟力量不斷對我施加的影響,”他寫道,使用現在時。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Sam Wood有一種特定的羞恥和自我厭惡的簡稱,滋養着拖延工作的習慣,當我們逃避工作以避免失敗時:冒名頂替綜合症。畢竟,如果我不是別人認為的那個人,如果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我被揭露的威脅——所有那些公開曝光和尖鋭批評——都表明我根本不應該嘗試。(我已經預料到,帶着恐懼,我未寫的書在 Goodreads 上的評論。)
插圖:彭博商業週刊的Sam Wood有一種特定的羞恥和自我厭惡的簡稱,滋養着拖延工作的習慣,當我們逃避工作以避免失敗時:冒名頂替綜合症。畢竟,如果我不是別人認為的那個人,如果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我被揭露的威脅——所有那些公開曝光和尖鋭批評——都表明我根本不應該嘗試。(我已經預料到,帶着恐懼,我未寫的書在 Goodreads 上的評論。)
有一位作家在應對 冒名頂替綜合症 這個術語的流行和其多重含義時,是萊斯利·賈米森(Leslie Jamison),她在二月份的一篇 New Yorker 文章中對此進行了詳細闡述。像奧德爾的書一樣,賈米森的文章沒有明確提到拖延,但其描述人們為了避免被發現自己所認為的失敗而不遺餘力的行為,與我所讀到的關於拖延者為何這樣做的內容很相似。
“冒名頂替者開始盡一切可能防止被發現她所有自我感知的缺陷,” 賈米森寫道。她寫道,一些女性“對自己的悲觀主義採取了一種魔法般的想法:敢於相信成功實際上會註定他們失敗,因此失敗必須被預期。” 或者,如果不是被預期,那就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
一些人説,冒名頂替綜合症的概念—就像時間的概念—非常白人化。賈米森,一位白人,提到了2021年《哈佛商業評論》中的一篇文章,標題為“別告訴女性她們有冒名頂替綜合症。” 文章的作者,賈米森指出,“認為這個標籤意味着女性正遭受自信危機,而未能認識到職業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所面臨的真正障礙—本質上,這將系統性不平等重新框定為個體病理。”
Jamison 還引用了一些人的話,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繁榮是建立在女性患有“綜合症”自我懷疑和自尊低下的概念之上的焦慮之中。 “感覺像個騙子確保我們會為無盡的進步而努力:更加努力工作,賺更多錢,努力比我們以前的自己和周圍的人更好,” 有人告訴 Jamison。 這種情緒在 Jenny Odell 的書中也不會顯得格格不入。
拖延可能只是騙子綜合症的一個症狀,當然不是最糟糕的一個,但是避免失敗的根本動力可能會對女性產生毀滅性後果,尤其是對女性而言。在 Lisa Damour 的 2019 年著作中, 壓力之下,這位暢銷書作者和臨牀心理學家談到了一羣女孩的流行病,她們對完美主義的執着使她們生病。 “在極端情況下,一些女孩決定只有在工作‘完美’時才能放鬆,” 她寫道,並補充説 “過度準備” 有助於緩解焦慮並贏得父母、同齡人和老師的讚賞。 “對於受到恐懼驅使的學生來説,這個系統非常有效。直到變得不可持續為止。” 並不是説青春期對我來説很容易,但至少我和我的同齡人沒有受到關於課外活動或從 10 歲起就要進哈佛的壓力。 (我是X世代的一員,儘管我們被指責懶惰,但在當前完美主義的氛圍中,我會説我們在成長時期很幸運。)
 插圖:Sam Wood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幾周前,我聯繫了傑夫·戴爾本人,想和他談談他的書和他的寫作過程。他有點像一個偶然的拖延先知(《紐約客》稱《純屬憤怒》為“一個避免拖延的經典”,而《Bookforum》則認為這就是寫拖延應該看起來的樣子,因為這就是在其甜蜜、讓人癱瘓的海洋中溺水的感覺),但聽到他寫那本書的過程對他來説既容易又有趣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他説他沒有“寫作障礙”,儘管他確實有時會拖延,有時甚至要過幾個月,甚至整整一年,才認真開始寫一本書。
插圖:Sam Wood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幾周前,我聯繫了傑夫·戴爾本人,想和他談談他的書和他的寫作過程。他有點像一個偶然的拖延先知(《紐約客》稱《純屬憤怒》為“一個避免拖延的經典”,而《Bookforum》則認為這就是寫拖延應該看起來的樣子,因為這就是在其甜蜜、讓人癱瘓的海洋中溺水的感覺),但聽到他寫那本書的過程對他來説既容易又有趣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他説他沒有“寫作障礙”,儘管他確實有時會拖延,有時甚至要過幾個月,甚至整整一年,才認真開始寫一本書。
他承認有一種恐懼,隨着年齡增長似乎變得更糟。 “當你年輕時,寫你的第一本或第二本書時,感覺真的很棒,”他説。“‘我想成為一名作家,寫這本書將使我成為一名作家。’”戴爾説。但後來,他説,當所有寫書的工作變得清晰時——“知道所有這一切工作的感覺——人會感到一種恐懼。”
這讓我想起我最近和一位建築師朋友的一次對話。他告訴我,上世紀90年代,他為好萊塢山丘的一位成功的劇本醫生和電視編劇(《辛普森一家》的創作者之一)設計了一個10英尺乘10英尺的“作家塔”。該塔包括兩個陽台,這樣作家就可以打開塔的玻璃門,享受20英尺的空間,可以在裏面來回踱步,試圖解決他寫作中的問題。塔內還有一張小牀供小睡。
這是他第一次説,他明白拖延可以被融入創造過程中——實際上必須被融入其中。“我覺得對我來説,這就是它的本質,”這位建築師説。“拖延是一種避免的方式—一種深深人性化的避免方式—避免製造醜陋的極端痛苦。”
同樣,戴爾正在進行一個關於他童年的項目,他説他會做任何他能找到的事情來打發拖延的時間:家務,打網球等等。然後,最終,他開始了。在這一點上,他盡力接受拖延是過程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極其低效的進行方式,但我似乎被困在其中。”
“到了一個地步,我發現不做比做更加無法忍受,”他補充道。
我開始有共鳴了。我的蘋果手錶震動了。該站起來了。